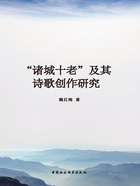
二 围绕“诸城十老”个体的研究成果
与围绕“诸城十老”群体的研究成果相比较,围绕“诸城十老”个体的研究成果却很丰富。目前学界对“诸城十老”个体的研究,用力并不均衡。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围绕丁耀亢和李澄中的研究方面。对刘翼明和张侗二人的研究,学界虽已有涉及,但只是做了简单的梳理,并未对其文学创作和成就进行深入研究。而对丘元武、张衍、徐田、隋平、赵清等人的研究,则更显薄弱,多是一些资料性的介绍而已。
(一)围绕丁耀亢的研究成果
20世纪初,学界对“诸城十老”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始于丁耀亢研究。更具体地说,应该是始于对丁耀亢小说《续金瓶梅》的研究。鲁迅先生称《续金瓶梅》“主意殊单简”[22],“一变而为说报应之书——成为劝善的书了”[23]。直到80年代,丁耀亢小说《续金瓶梅》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90年代,丁耀亢的戏剧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1997年5月18日到20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和诸城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在丁耀亢家乡诸城顺利举行。1998年,李增坡主编的本次会议论文《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4]出版,标志着丁耀亢研究有了专门的研究成果。1999年,张清吉点校的《丁耀亢全集》[25]出版,为学界进一步从事丁耀亢研究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文献资料。此后,不仅围绕丁耀亢小说和戏剧的研究、丁耀亢生平与交游的研究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还开启了围绕丁耀亢诗歌的研究并诞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1.围绕丁耀亢小说《续金瓶梅》的研究成果
围绕丁耀亢小说《续金瓶梅》的研究,学界主要探讨了《续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写作时间、版本等问题,并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
关于《续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学者们的观点略有不同,但大都特别肯定《续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如黄霖的《〈金瓶梅〉续书三种·前言》,认为《续金瓶梅》是对明朝灭亡教训的总结,对清朝统治者的野蛮行径充满仇恨,是爱国爱民的表现。[26]方正耀的《明清人情小说研究》,认为《续金瓶梅》“侧重描写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动乱,揭示民族矛盾”,并“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意识”。[27]时宝吉的《〈续金瓶梅〉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华》,认为《续金瓶梅》是“对明朝覆亡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体现出作者追求民族自由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操”。[28]周钧韬、于润琦的《丁耀亢与〈续金瓶梅〉》,认为《续金瓶梅》“宣传一种腐朽的宗教观念:因果报应”[29]。张俊的《清代小说史》,认为《续金瓶梅》的意义和独到之处在于:借因果报应,劝人止恶为善,发展了《金瓶梅》题旨;表现了作者忧患时局、痛悼故国之情;框架结构及人物描写,颇有特色。[30]王汝梅的《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创作及其小说观念》,认为“作者把叛徒蒋竹山、张邦昌写得没有好下场,对抗金名将韩世忠、梁红玉则热情歌颂,表现了作者拥明抗清的民族思想”,“有厚重深沉的历史感”。[31]罗德荣的《〈续金瓶梅〉主旨索解》,认为《续金瓶梅》作者提出的“惜福”主张,重在完善自我,重塑民族之魂的思考。[32]袁世硕的《续金瓶梅前言》,认为“演因果报应的故事情节中,也正寄寓着对卖国通敌者的鞭挞”[33]。
关于《续金瓶梅》的写作时间,学者一致认为当在顺治年间,但对成书的具体年份,则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说法:(1)顺治十八年(1661)说。黄霖的《金瓶梅续书三种·前言》,首次提出顺治十八年说。[34]其后刘洪强的《〈续金瓶梅〉成书年代新考》,依据《续金瓶梅》第二回已经出现“宁古塔流人”、而历史上第一起“宁古塔流人”发生在1655年等材料,指出丁耀亢开笔不会早于1655年,进而又结合其他证据,认为《续金瓶梅》的最后成书当是1661年。[35](2)顺治十一年至十五年(1654—1658)说。张清吉的《醒世姻缘传新考》,首次提出顺治十一年至十五年说。[36]欧阳健的《〈续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认为丁耀亢在1648—1654年任北京旗官时已构思动笔,在1654—1658年任容城教谕时撰写完成。文章反驳了黄霖、石玲的观点,基本赞同张清吉的意见。[37](3)顺治十七年(1660)说。石玲在《〈续金瓶梅〉的作期及其他》中,首次提出该书是作者在顺治十七年客游杭州时所作。[38]与之观点一致的还有如下诸家:孙玉明的《〈续金瓶梅〉成书年代考》,大体同意石玲的“1660年秋之前”说,而反驳了张清吉的观点。[39]王瑾的《试论〈续金瓶梅〉的创作年代》,反驳了黄霖、张清吉的观点,赞同石玲、孙玉明的论点,并以《顺康年间〈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受审案》中“该书撰写于顺治十七年”作为论据,得出成书于1660年。[40]而安双成翻译的《顺康年间〈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受审案》,其中详细记录了丁耀亢的供词:“此《续金瓶梅》十三卷书,乃为小的一人撰写。小的于顺治十七年独自撰写,并无他人。”[41]
关于《续金瓶梅》版本的问题,有王运堂、王慧《略论馆藏足本〈续金瓶梅〉》[42]一文。该文在爬梳国内现存《续金瓶梅》各版本的同时,重点描述了山东图书馆所藏有的残本和足本两个版本。
2.围绕丁耀亢戏剧创作的研究成果
学界在研究丁耀亢小说的同时,也围绕丁耀亢戏剧主题、戏剧风格、戏剧观念等问题进行探讨。如周妙中的《清代戏曲史》一书,认为丁耀亢的剧作“不论从思想性看还是从艺术性看,都不逊于当时的名家,是个饱受战火之害的诗人兼戏曲家,情况和吴伟业极类似”,且“他的剧本是会在舞台上取得良好的效果的”。[43]郭英德的《明清传奇综录》,对丁耀亢的四部传奇分别就其版本、故事源流及出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进行了详细的文献梳理考辨。[44]石玲的《丁耀亢剧作论》,认为丁耀亢的剧作“反映了丁耀亢迷茫与痛苦——怀旧与动摇——承认现实——争取仕进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般在明末未出仕但已成年的汉族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过程”[45]。黄霖的《略谈丁耀亢的戏剧观》,指出丁耀亢的戏剧观主要包括自然观、布局论、悲喜剧论三个方面。[46]陈美林、吴秀华的《试论丁耀亢的戏剧创作》,认为丁耀亢剧作在内容上具有浓厚的“遗民情结”,又表现出“入世精神与出世情怀的矛盾”,其剧作局限于“因果报应色彩浓厚”、有“虚无思想”;在曲词、结构布局、人物塑造等方面有较高艺术成就,不足之处是“以写史之笔写剧,基本上是案头之作,很少考虑演出因素”。[47]孔繁信的《丁野鹤戏曲创作简论》一文,认为丁耀亢的《西湖扇》,对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有影响;《表忠记》“题材布局和组织结构上则匠心独运”,超过了同题材的《鸣凤记》;《赤松游》表现了作者“功成身退”、“消极避世”的思想;《化人游》则是作者逃避现实之作。[48]徐振贵的《孔尚任何以用戏曲形式写作〈桃花扇〉》一文,认为丁耀亢《西湖扇》对孔尚任《桃花扇》创作的影响表现在七个方面:剧名相似;两剧之扇,都起到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都是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剧首都附有所据事实;两剧都有“入道”情节;《西湖扇》的《窃扇》中顾史道庵寻访宋娟娟与《桃花扇》之《题画》中侯生媚香楼寻访李香君告白情境相似。[49]廖奔、刘彦君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第四章第一节“丁耀亢”中,认为“他的传奇创作,不但给我们以经由其场面与情境渠道来认识明清易代时期丰富社会生活的可能性,而且通过其中的人物世界,以及通过渗透在作品形象中的作者的心理倾向,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当时文人一些重要的精神侧面及其心理体验”[50]。
3.围绕丁耀亢诗歌创作的研究成果
学界对丁耀亢诗歌的研究起步较晚。2001年之前,仅有张维华的《跋丁耀亢的〈出劫纪略〉和〈问天亭放言〉》[51]一文,主要探讨了丁耀亢《出劫纪略》和《问天亭放言》对明末清初的许多事件有存史之功。2001年之后,关于丁耀亢诗歌的研究论文逐渐增多,研究内容也逐渐深入。如王瑾的《论丁耀亢诗中的人生感受》[52]一文,将丁耀亢诗歌的主题概括为恬淡的情怀、乱世的悲音、逃禅的无奈三大主题。王慧的《山左诗人丁耀亢》[53]一文,则结合丁耀亢的生平介绍了其不同时期的诗集,认为丁耀亢仕宦时期的诗歌充满沉郁悲凉的风格。陈清的《丁耀亢诗歌研究》[54]一文,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角度,对丁耀亢的诗歌进行了全面分析。魏红梅的《简析丁耀亢诗集〈问天亭放言〉》[55]一文,认为《问天亭放言》的内容可概括为山居乐趣、隐逸情趣,落第悲伤、失意惆怅,关注现实、以诗记史三类,反映了丁耀亢既想隐居山林又不能忘怀世事的矛盾心态。张崇琛的《丁耀亢佚诗〈问天亭放言〉考论》[56]和《丁耀亢的两首佚诗》[57]、周洪才《关于丁耀亢佚诗集〈问天亭放言〉的几个问题》[58]、刘洪强《〈丁耀亢全集〉补遗》[59]等,则围绕丁耀亢的佚诗进行了相关研究。
4.围绕丁耀亢本人的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学者对丁耀亢的家世、生平、交游等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陈金陵的《丁耀亢与〈出劫纪略〉》[60]、栾凤功的《也谈丁耀亢与〈出劫纪略〉》[61]、石玲的《明末清初作家丁耀亢生平考》[62]、黄霖的《丁耀亢及其〈续金瓶梅〉》[63]、郝诗仙和郭英德的《丁耀亢生平及其剧作》[64]等。90年代,不仅围绕丁耀亢研究的论文逐年增加,其中包括硕博论文,如刘洪强的博士论文《丁耀亢文学创作研究》、范秀君的博士论文《丁耀亢研究》等;还出现了一些研究专著,如张清吉的《丁耀亢年谱》、胶南市史志办公室编写的《丁耀亢生平纪略》等。
张清吉的《丁耀亢年谱》[65]是研究丁耀亢生平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以丁耀亢的著述为主要依据,大致勾勒了丁耀亢一生的行踪。石玲的《明末清初作家丁耀亢生平考》[66],考证和分析了丁耀亢的家世、生卒年代和生平等。胶南市史志办公室编写的《丁耀亢生平纪略》[67],通过爬梳丁耀亢的作品,详细地介绍了丁耀亢一生的经历和交游、文学创作活动。王瑾的《丁耀亢交游考略》[68]、马清清的《丁耀亢交游考》[69]等,则考察了丁耀亢的交游对象。刘洪强的博士论文《丁耀亢文学创作研究》[70],上编分为四章,分别讲述丁耀亢的生平与家世、《续金瓶梅》研究、诗歌研究、戏曲与鼓词的几个问题,各章均有不俗见解;下编所列丁耀亢年谱,既依据丁耀亢的作品,又从丁耀亢朋友的作品找寻有用的材料,以充实丁耀亢年谱,弥补了张清吉先生《丁耀亢年谱》的不足。范秀君的博士论文《丁耀亢研究》[71],通过全面考察丁耀亢的生平和创作,既梳理了明末清初之际北方中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又考察了处于易代之际文人的生存心态、对时代的文化反思及文学创作的特点等问题。黄琼慧的《世变中的记忆与书写:以丁耀亢为例的考察》[72]一书,以“世变”、“记忆”、“编写”为关键词,通过重读丁耀亢的《天史》、《出劫纪略》、《续金瓶梅》等作品,考察丁耀亢在不同时期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状况的变化,以观察世变、记忆以及编写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围绕李澄中的研究成果
学界围绕李澄中的研究,始于对其杂著《艮斋笔记》的研究。主要有白亚仁的两篇论文:《略论李澄中〈艮斋笔记〉及其与〈聊斋志异〉的共同题材》、《〈林四娘〉故事源流补考》。前文主要介绍了李澄中《艮斋笔记》的大致编定时间以及主要内容,认为“李澄中和蒲松龄虽然不一定有过直接的接触,但是两个作家都生活在清初的山东,因此他们所听到的社会新闻自然有不少类似之处”[73]。后文则认为李澄中不仅写过林四娘的故事,还记录过林四娘创作的诗歌。[74]
此后,围绕李澄中生平及其文学成就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王宪明的《沧溟后身 山左鼎足——浅论李澄中的文学成就》[75]一文,考察了李澄中对李攀龙的认同以及李澄中与王士禛的关系,并综述李澄中的文学成就,肯定他的赋作。王宪明主编的《李澄中文集》[76],其中有他本人所作序和《李澄中年谱简编》,不仅简述了李澄中的文学成就和影响,还以年谱的形式勾勒了李澄中一生的主要活动。尚金玲的《山左诗人李澄中及其诗歌研究》[77],可以说是系统研究李澄中生平以及诗歌创作成就的第一篇文章。该文介绍了李澄中的家世生平以及交游活动,重点分析了李澄中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魏红梅的《李澄中云南之行考略》[78]一文,考察了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十一岁的李澄中受命典云南乡试的行走路线以及留下的轶事和作品《滇行日记》、《滇南集》等。陈冬梅的《“博学鸿儒”李澄中研究》[79],则论述了李澄中的文学成就和学术贡献。于海洋的《论李澄中诗学观》[80],认为李澄中在诗歌创作上以杜甫为宗,取法盛唐,具有通变的诗学观。
(三)围绕“诸城十老”其余成员的研究成果
围绕“诸城十老”其余成员的研究成果,目前仅有张崇琛的《张石民与张瑶星及孔尚任的交往》[81]一文。该文既考察了张侗南下金陵拜访张瑶星的过程,又考察了张侗与孔尚任的交往大概,认为张侗、张瑶星和孔尚任都有遗民情怀。
需要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诸城十老”开始进入了各类文学史,尤其是山东文学史的书写范畴。如李伯齐的《山东文学史论》[82]第十一章“明清时期的山东文学(中)”之六“丁耀亢与诸城诗人”,介绍了丁耀亢、李澄中、刘翼明等人的经历和文学创作。其后,李伯齐的《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83]第十二章第二节“清初山左诗坛”中,专门介绍了“丁耀亢和清初诸城诗人”,重点分析了丁耀亢在明清易代之际的矛盾心态以及诗歌创作,简要介绍了丘石常、李澄中的诗歌创作。许金榜主编的《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第六章第二节“清初诸城重要传奇作家丁耀亢(一)”、第三节“清初诸城重要传奇作家丁耀亢(二)”,详细地分析了丁耀亢《化人游》、《赤松游》、《西湖扇》、《表忠记》等剧作的创作成就。王恒展主编的《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第八章第三节之二“丁耀亢与《续金瓶梅》”,分析《续金瓶梅》的成书、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王琳主编的《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第五章“清代山东散文”第五节中,介绍了张侗的《卧象山记》和《蓬莱阁记》等散文。王振民主编的《潍坊文化三百年》[84]第四章“文学”之四“明清之际诸城的文学社团及群体”,介绍了“东武西社”、“诸城十老”、“张氏四逸”的生平及文学创作。周潇的《明代山东文学史》[85]第十四章第五节“丁耀亢与诸城作家群”,介绍了丁耀亢、丘志广、丘石常、刘翼明和李焕章五人的文学成就。
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的爬梳,可以看出,学界对“诸城十老”的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重个体研究而轻群体研究;二是对“诸城十老”个体的研究,用力也很不均衡。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丁耀亢与李澄中二人身上,而对其他成员关注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