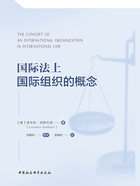
第1章 导论
1975年《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以下简称《1975年国家代表权维也纳公约》)是国际组织法获得国际法独立部门尊严的历史进程中的第一个正式产物。[1]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仅有关于国际组织的零散研究,关注的是与一些特定机构有关的具体问题;没有尝试过进行一般性的分类。诸多的国际组织本身就是一种碎片化的现象,从行政性联盟和国际委员会到国家之间辩论国际政治的会议,不一而足。只是在《1975年国家代表权维也纳公约》之前的10年中,国际组织法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依靠比较方法来解决诸如获赋职能、法律人格和豁免权等共同事项。[2]随着《1975年国家代表权维也纳公约》的出台,不同的机构首次受到相同的管理框架的约束,但不过是在外交关系法领域。《1975年国家代表权维也纳公约》表明,对具有共同根源和共同目标的一种独立现象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1975年国家代表权维也纳公约》的故事还是一个失败的故事。该公约代表了比较方法的失败;这种方法试图制定一个适用于某一大类国际组织的一般性法律框架。事实上,《1975年国家代表权维也纳公约》的全面性适用范围是建立在对“国际组织是什么”缺乏任何批判性讨论的基础之上的。为了实现一份技术文书的有限目标,即划定管理成员(国)常驻代表团的法律框架,之前关于国际组织之间结构差异的辩论遭到了淡化。
在出台《1975年国家代表权维也纳公约》的工作过程中,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采用了一种推理模式,并在其关于国际组织的其他项目中予以应用。根据这种模式,一个特定项目,无论是外交关系、条约法还是国际责任法,其目的都不是界定国际组织是什么,而是提供适用于该项目所关注的特定的、有限情形的一套规则。例如,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以下简称《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目的不是界定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从何而来;相反,相应项目假定存在这种人格,因为这种人格使条约得以缔结。[3]同样,关于责任的项目其目的不是确定国际组织制定的法律是否是国际法;相反,它是从存在某一项国际义务的假设前提出发。[4]
简而言之,应该识别适用于国际组织的一个综合性法律框架的那几份法律文书,是建立在缺乏对“国际组织是什么”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下列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国际组织法不能满足国际组织具有一种突出作用的这一世界性期望。
事实上,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几位特别报告员曾试图就如何对国际组织予以概念化进行辩论,但是他们从未成功地达成共识。早在1958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在讨论条约法的编纂问题时,就邀请国际法委员会在国际组织法方面加倍努力,并开始研究“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庞大专题。[5]阿卜杜拉·埃尔-埃利安(Abdullah El-Erian)被任命为特别报告员,他于1963年提交了第一份报告。[6]
埃尔-埃利安以对国际组织定义的演变开展研究作为开端,识别了三种“类别”的定义。
第一种试图将国际组织纳入当时的国际法经典范式之中。迪奥尼西奥·安齐洛蒂(Dionisio Anzilotti)[7]和他关于国际组织是其成员(国)的集体机关的理论是典型事例。[8]根据这一概念化,国际组织不是独立的实体,仅是代表其成员(国)的集体意志。在同一主题下,埃尔-埃利安识别了由凯尔森(Kelsen)提出的另外一个定义:
一个有组织的国际社团是由一项条约建立的;为了实现建立该国际社团的目的,该项条约设立了该国际社团的特别机关。该国际社团是一个“国际的”社团;它不具有国家的性质……[它]是一个国际组织。与联邦制国家相反,它是一个邦联。[9]
第二种埃尔-埃利安将其模糊地界定为:“使用我们对这种现象的当代理解追溯过去的某些经验,从而以今度古。”[10]他引用了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的研究成果;后者将国际组织定义为:
国家之间各种形式的合作,试图通过它们的联系在国际环境中实现某种秩序,由国家的意志创建,并在国家是主要法律人格者的环境中运行。[11]
在字里行间,这种定义试图将一个单独秩序的存在与其从国际法中的衍生物予以结合。
第三种的基础是,试图分离并强调某些被认为对定义国际组织至关重要的要素。[12]不同的学者依赖不同的基本要素;不过,他们通常考虑宗旨、条约基础、常设性特征、拥有独立于成员(国)的机构以及拥有法律人格。在第三种定义标题之下,埃尔-埃利安引用了数位作者的定义,特别是聚焦于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条约法的工作。[13]
对这一主题的宽泛理解使埃尔-埃利安为国际法委员会的这项未来工作制定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议程。在他的初步意向中,下面是他接到的任务:
(一)第一组任务——国际法律人格的一般原则,其中包括:(1)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概念的定义;(2)法律能力;(3)缔结条约的能力;(4)支撑国际求偿的能力。
(二)第二组任务——国际豁免权和特权,其中包括:(1)国际组织的特权和豁免;(2)与国际组织有关的使领馆机构问题;(3)外交会议。
(三)第三组任务——特别问题:(1)关于国际组织的条约法;(2)国际组织的责任;(3)国际组织之间的继承。[14]
然而,国际法委员会大大缩小了该项目的范围,优先考虑外交关系法适用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15]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1967年)中这样总结:他所组织的关于国际组织法律人格一般原则的讨论,在委员会内部引起了很大争议。[16]在第三次报告(1968年)中,他建议将国际组织定义为“根据条约建立的国家联盟,拥有组织宪章和共同的机关,并拥有不同于其成员国的法律人格”[17]。如前所述,国际法委员会拒绝接受对国际组织进行界定的必要性,并拒绝纳入这一定义。不过,它“认为,这种详细的定义目前并不必要,因为它[委员会]在目前的工作阶段并不处理国际组织本身的地位,而只是处理国家派遣到这些国际组织的代表的法律地位”[18]。最终结果是,国际法委员会在处理外交关系法专题时,避免任何理论问题,而是将重点放在关于成员(国)常驻代表团的实际问题方面。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条约法的当代工作表明,学者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如法律人格的属性、发展内部秩序的能力以及国际组织所制定法律的属性。[19]《1986年维也纳公约》表明它未能成功地解决透明机构面纱的困境这一问题;该困境使国际组织既不像国家那样自成一体,也不像条约缔约方会议那样对国际法完全开放。[20]
在国际组织数量激增的历史时期,其规范性基础已经开始显现出其自身的缺陷。比较主义者的方法提示,它虽然足以提供对共同特征的描述,但是完全不足以解决作为国际组织法特征的基本法律难题。因此,只能在一般性条款中找到一致意见,而这些条款又过于笼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国际组织,除了它是政府间组织的简称外,法律界人士缺乏一个一致同意的定义。[21]
总之,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框架仍然限于一套没有明确适用对象的规则。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国际组织缺乏共同的理解,不同的路径被混乱地组合在一起。简而言之,我们不知道国际组织是什么。特别是,《1975年国家代表权维也纳公约》开启了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在本书中将之定义为这样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即要么从国家中心的视角,要么从组织中心的视角来看待国际组织。下面的讨论旨在分析不同的概念化,评估是否存在一般性管理框架,以及提供国际法中国际组织概念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