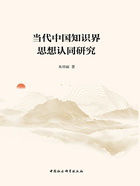
三 相关概念辨析
(一)相关概念辨析
1.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文化蕴含的概念,但如何界说“知识分子”却众说纷纭。诚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6]“知识分子”的“根本”在于助力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知识”,是否拥有“知识”是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然而,作为文化身份标志的“知识”并非经验观察得来的、与他人无涉的纯粹客观知识,而是经由理性提炼、面向人类社会的规范性知识,具有联结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公共性价值。因此,知识分子是以文化知识传承的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关怀社会发展的特殊阶层,追求真理和担当道义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格。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诞生于20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风雨飘摇的年代,特殊的历史文化境遇使得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必然要触碰现实的政治问题,可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又与从事实践的政治活动家明显不同,因此,“议而不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实现抱负的重要途径。面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时代课题,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些有知识的群体就似乎注定要与政治社会发生某种必然联系,他们或者以批判的姿态保持一种对政治社会无条件地追问的权力,或者通过对政治社会的介入成为联系和调节各种社会集团的‘中介’。”[37]钱穆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其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的鲜明特点:一是“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性。……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38]。二是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大群。……肯把自己个人没入在大群中,为大群而完成其个人”[39]。因此,在知识分子的理想中,政治关怀与人文精神的理念是一致的,政治若脱离人文之中心,则会连技艺专长都不如。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纯粹的阶级概念,也不是纯粹的学术概念,更不是一个纯粹的职业概念,而是蕴含内在张力的矛盾统一体。考察知识分子问题要面向客观的矛盾与客观的实际,这些矛盾与实际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与公共性。知识分子首先是具有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的群体,不同的专业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职业选择,而专业恰恰也是知识分子在公共舆论空间和公共社会生活确立文化权威的知识前提。但仅仅囿于专业知识的专家却不能够称其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要通过社会认同来成就其知识体系与思想主张,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在于其专业基础上的公共关怀,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社会功能与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客观真理的基础上,离开客观真理谈论公共关怀,必然会走向歧途。
第二,知识分子的阶级性与理想性。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双重的,即阶级身份和文化身份。从阶级身份来看,在依然存在阶级和阶级冲突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超阶级”而独立存在,必然归属于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知识分子在其文化理念的表达中很难完全避免阶级性、党派性立场。但是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在于其阶级身份可以转换,即从属于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的知识分子可以再次选择或者背叛自己的阶级立场。从文化身份来看,具有不同阶级属性、阶级立场的社会成员可以共同组成知识分子阶层,联结的纽带就是超越现实的道德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总是试图超越个体或阶级集团的利益藩篱,以谋求终极关怀和人文精神为价值寄托。“处于某一社会阶层或集团的知识分子固然未必归属于自己所处的阶层或集团,但却无法不认同任何阶层或集团,而其观念、理想,则每每折射了其社会认同。”[40]正是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被称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公平正义的代言人。知识分子阶级性与理想性的内在紧张表明,只有选择进步的阶级立场、代表先进的文化方向,才能真正实现其崇高性、人民性的理想追求。
第三,知识分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国走向何处”“索我理想之中华”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时代课题,民族性与世界性构成知识分子积极求索的两重维度。一方面,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与民族责任感,往往将其个体生命熔铸于深沉的国家使命之中。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是第一生产力的积极开拓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积极促进世界各国不同文明形态的对话交流。因此,任何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名义拒绝世界交往,以及任何以世界交往的名义拒绝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的做法,都是偏狭的,无助于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实现。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进步知识分子之所以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为知识分子指明了实现“世界大同”与担负“家国情怀”的现实途径。
2.“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关怀品格,因此,公共关怀是知识分子突出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特征。但是具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并不等同于西方特殊语境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特殊群体。
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是对当时西方社会工具理性对知识价值的戕害、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危机、知识分子批判意识式微等现象的反思与反抗。因此,1987年美国学者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就是对知识分子“公共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呼唤。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将知识分子理解为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的角色使命。知识分子“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41]。
西方社会将“对抗”“批判”“正义”“良知”理所当然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标签,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和公共使命。从根本上说,这源于西方国家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的对抗。按照西方社会的认识逻辑,国家代表着理性与社会普遍利益体系,而市民社会则是感性的私人利益体系。所以,国家要为市民社会“立法”、建立秩序、确定规则,以此限制市民社会的无序活动和竞争;而市民社会作为私人利益体系,存在斗争冲突、剥削压迫、尔虞我诈,如果没有有效的理性规范对其进行约束,市民社会必将走向自我毁灭。质言之,国家与市民社会、普遍的公共生活与特殊的个体存在之间必然处于对抗性的关系网络之中。“‘公共知识分子’所表征的公共理性之所以认为自己有可能代表另一种政治文化,是建立在西方权力分散的观念和体制上,建立在阶层分化和阶级利益的对抗上。”[42]然而遗憾的是,现代西方社会在目睹了知识分子的沉沦以后,对公共知识分子照亮公共空间的质疑与批判之声也接踵而至,频频发出“最后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衰败论”“知识分子死亡论”的哀叹。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则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假借“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的外衣表达其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言论。中国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片面强调“超阶级”的价值中立和社会批判精神,以“离经叛道”的“惊人”见解表现其“正义”立场,博得民众在不明真相情况下的自发性、广泛性认同。恩格斯曾经说过:“‘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象’。”[43]实际上,“公共知识分子”以价值中立和“去意识形态化”掩盖其特殊的利益诉求,“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正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