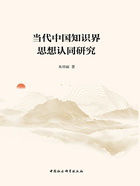
绪论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法国史学家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1]但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思想影响力的文化主体活跃于历史舞台,却是近代“知识就是力量”以后的事情。从词源上来看,知识分子概念有三个源头,分别是俄国、法国和英国。无论是俄国19世纪30—40年代彼得大帝派出学习西欧先进文化理念、回国后秉持现实批判精神的贵族青年,还是法国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中参与社会事务的左拉式知识精英,以及英国1907年巴林(M.Baring)最早使用该词指涉那些拥有文化与政治主动性的阶级,西方的“知识分子”词源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谱系:“对抗”“批判”“正义”“良知”,这些似乎构成了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身份标签。
从普遍的、一般的意义而言,知识分子是指在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中具有较高程度的文化和专业知识,他们以创造、积累、运用、传播文化知识为专门职业。因此,以知识、思想的力量,关怀社会公共生活,构成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品格。可是,随着知识的增长,人们越来越困惑、迷茫,到底哪些人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这些人该如何守护知识分子精神?对此问题的回答,却有着极强的民族文化差异性。
人们在使用知识分子概念时,无法回避和割舍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所处时代。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定也是不同的。在近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常常以批判现实的方式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作出努力。在我国古代,与“知识分子”含义相近的概念是“士”,即通常所说的“读书人”“士大夫”。然而,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对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权具有依附性。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依附国家政权的“士”,也不同于西方社会自由漂浮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掌握较多科学文化知识的工人阶级,他们以所知、所学、所思、所想贡献和服务社会。
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中华民族涵养了中华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赓续、薪火相传,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信仰,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重道义、勇担当,坚守正道、追求真理,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座巍然屹立的精神丰碑。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到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两弹一星”元勋,以及近年来涌现的以黄大年、李保国、钟扬等为代表的新时代优秀知识分子,他们的名字在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熠熠生辉,标示出爱国奋斗精神的历史厚度与时代高度。正是他们,在我国知识界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不同领域,以知识积累和文化传承为载体,弘扬着中国文化,讲述着中国故事,践行着中国价值,塑造着中国精神,凝聚着中国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中国精神,伟大的征程需要伟大的中国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既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与征程中,广大知识分子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投身创新发展实践,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不断增加知识积累,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不断增进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思想认同,既是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殷切期盼,也是广大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新时代的主体自觉。
在知识创新与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密切关联的时代条件下,知识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理想位置如何确立?知识分子应以怎样的价值导向进行知识创新与文化传承?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必然涉及知识分子思想认同。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价值认同,是知识分子进行知识创新与文化传承的精神动力,也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与文化安全的“隐形资产”。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养的社会阶层。从应然层面来看,知识分子理应更加“倾心”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与解放,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恰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从实然层面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既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又有追求道义的责任担当,以求真扬善达美的文化品格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都表现出较高程度的自觉与自信,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发挥着文化引领的积极作用。广大知识分子深沉的文化自觉表明,坚持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立场,是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也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精神文化力量。
然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今世界,以“普世价值”和形形色色文化外衣裹挟的意识形态对抗与对话并存,知识分子无可逃遁利益博弈、文化冲突与国家安全。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恰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由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层多样,当代中国知识界呈现出思想认同多元多样、同中有异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在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愈加学术化、文化化的情况下,受敌对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错误社会思潮的蛊惑,知识界少数“文化人”对于自身工人阶级身份认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模糊、质疑、疏离甚至背叛倾向。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塑造整个社会的精神氛围以及知识版图的过程中,“如何兼及自信与自省、书斋与社会、思想与学术、批判与建设,将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难题”[3]。
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不仅寄托着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主体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多棱镜式思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不同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人心角逐与认同状况。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总体状况,不仅是团结和引领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深入挖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资源以及提升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的战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