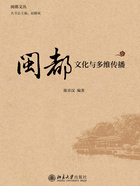
第一辑 长廊辞赋
长廊文化是二十一世纪伊始福州文化强市的一大创造。分布在各大公园和风景区的长廊让市民在欣赏名山胜水的同时走进都市的人文深处,与历史摩挲,同古人对话,认识“往古来今”,把握“贯古通今”,努力“灿古烁今”。
福州建城两千两百周年是集聚都市能量、彰显文化实力的绝佳机会,主官们不会轻易放过这“百年一遇”的城庆文化节点。继大型歌舞晚会“左海千秋”获得成功之后,市里一鼓作气,在闽江北岸的闽风园开辟了一条长二百二十米、高五米的福州历史文化长廊,这条长廊既是对灰色的水泥砂石堤坝的“艺术地遮羞”,又依托以花岗岩为载体的高浮雕带领人们进入时光隧道,知我福州并爱我福州。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笔者来福州任职之后,即有机会参与一系列建城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其中最“滋补”的是笔者牵头组织编纂的“可爱的福州”丛书,这套丛书的编纂工作给笔者狠狠地补了一课。文化长廊的艺术指导工作与“左海千秋”的案头创作和舞台演绎有所不同,文化长廊的设计是一项“软硬兼施”的大地艺术,很新颕,很有难度,也很刺激。
一座城市的山川灵秀、历史沿革、重大事件及人物风流,笔者要用几百字的篇幅概其要、约其心、述其成、点其睛,谈何容易?大概只有“简约不简单”的赋体文方可胜任。有道是“文无定法,诗无达诂”。体裁与题材的遇合可以是不期然的,但不排除早有因缘潜在。笔者在创作上原也不太“挑食”,先后出版过散文集、随笔集、特写集、小报告文学集、长篇报告文学、长篇儿童文学,以及美学类、文史类、书法类的图文书。因时因地,顺势而上,转身捡起“赋”这种旧文体,并非见异思迁、以退为进,而是机缘巧合、以攻为守。
用“赋”的形式来写长廊卷首的前言可谓是一次大冒险、大考验。好在早年“书香门第”种下了种子,“老三届”也打下了基础,当了“范进”之后更恶补了训诂学、修辞学、逻辑学乃至古文字学之类的冷门。不惑之年大胆著述《美感百题》,幸得美学泰斗王朝闻题识嘉许;知天命后则有别于许慎,写了一部《说字写文》,又蒙北大教授谢冕作序砥砺。于是窃想,相如赋上林,杨雄赋甘泉,班固赋西都,张衡赋西京,更有左思的三都之赋,皆能以不多的文字极写一城一地的乾坤,咱这五度为都、六次扩城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何不能“借旧瓶装新酒”?只要“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便不至于太离谱。我打着气迎难而上,于是平生第一篇骈体文《闽都赋》应命而作、应运而生。二十一世纪伊始,八百余言的《闽都赋》在“福州历史文化长廊”卷首正式面世。它概括了闽都古城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也开辟了个人创作生涯的“赋里春秋”。 《闽都赋》被光明日报社发起的全国“百城赋”征文专栏选中,易名为《福州赋》全文刊行,并获“首赋”之誉。
《闽都赋》开篇一段这么写着:
八闽雄都,神州名府。北枕莲花,南控五虎。右擎翠旗,左标石鼓。拥三山入怀中,抚二塔于膝下。挈西湖而邀闽水,踞六鳌以望双龙。卧野环山,无数春声秋色;派江吻海,不尽汐落潮生。城内河道纵横,宜商宜旅;郭外港流吞吐,可运可渔。灵山秀水,形胜东南。有福之州,斯之谓也。
一座千年古城,开天辟地的人物首先应重笔而书,于是写道:
钟灵之地,人龙出焉。先民尊蛇为图腾,铸剑为神器,渔猎山伐,刀耕火耨,初展闽地生机。汉无诸东冶为都,建城置垒,拓土开疆,共缔闽越春秋。晋严高筑子城,并水网,凿东西两湖。五代王审知,辟港通津,引舶入市。复于罗城之外,再筑夹城。百雉千堞万灶烟,蔚为大观。
接下来是一个关于古城文明演进的大问号——“闽之山,何苍苍;闽之地,何苒苒。”问题由自己提出,并即席作出解答。其抵达的精准与表达的熨帖曾被北大谢冕教授特别地引出并予以点赞:
闽之山,何苍苍;闽之地,何苒苒。中原士族,数度南奔。文化交汇,俊彩星驰。唐宋以降,文风日炽;书声盈巷,科甲联芳;刻书成业,闽学蔚起。路逢十客九青衿,海滨邹鲁,誉之当矣!城市管钥,亦多儒士,君谟栽松,伯玉植榕,江山文章,皆成锦绣。时绿榕荫里,人物往来,千家沽酒,百戏开台,欣欣乎向荣。或曰:人间即此升天近,谁复乘槎赋远游?
长廊文化影响之大令我始料未及。继福州历史文化长廊之后,市里又接连开辟了五条文化长廊。从西河园至金沙园的那段1800米的长堤被开辟为“福州名人名言长廊”,这是第二条长廊。这条长廊以石材刻字等形式展示了六十余位福州古代和近现代名贤立德、立功、立言的经典。第三条是长1800米的“福州历史纪事长廊”,这条长廊同样利用闽江南岸江堤将福州历史编年大事记、重大事件(包括天灾人祸)等一并呈现。第四条是南江滨公园的“福州国际城雕长廊”。长廊不一定整体取直,这条长廊就借用了中国画“散点透视”的原理,让单体作品巧妙安置于曲径通幽的林荫、草甸、道旁,形成自然与人文掩抑相生的走廊景观。于是四大洲十七个国家的七百多件应征城雕方案云集福州,其中有六十余件作品脱颖而出。艺术家汇聚闽江之畔,于同一日期、同一地点同时开凿,作品琳琅满目、精彩纷呈。
之后开辟的两条长廊,一规则,一不规则。规则的是长150多米的“船政文化长廊”,该长廊采用的是石质浮雕的形式,描绘了发生在“中国塔”(马尾罗星塔)下的百年船政风云。不规则的是鼓山上的“中国摩崖题刻长廊”。达摩十八景区新增了若干摩刻,其内容以闽都古今名人哲语、诗句为主,这些摩刻与万松湾古道和涌泉寺喝水岩的老碑林连成一脉,形成一条曲径通幽的“中国摩崖题刻长廊”。这两条不同样式的长廊被开辟后,出现了一个共同的文化需求,就是各要一篇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赋文来“压阵” 。
有了《闽都赋》的成功经验,《马江赋》 《鼓山赋》的撰写任务自然又都落在笔者肩上。虽说是轻车熟路、能者多劳,并且当时我还兼任船政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也觉责无旁贷,但《马江赋》的创作体验与《闽都赋》完全不同。一抚摸到几百多年前的那段史实,我就不能自已!领风气之先的那批左海精英的伟业与豪情、行止与胸襟足以让后人为之匍匐。
适格致关头,人神共察。强国利兵,梦醒海岬。左文襄奏兴船政,但以一篑为始基;沈文肃倡办学堂,敢致九译之新法。认真下手,践师夷制夷之远谋;仔细扪心,书铸舰铸人之神话。
然而,1884年的中法马江海战改变了这一切:
时光绪甲申,法夷称兵。先扰鸡笼,后袭磨心。所以有恃无恐者,惟炮利船坚。马江军民,铁石同心。共赴国难,烈士逾千。忍此国之大殇者,将安得永年?幸矣马限山,有缘掩藏忠骨;恸哉我子弟,何辜喋血门前!恨腐朽清廷,积贫积弱;惜未丰羽翼,堪恤堪怜。昭忠祠在,浩气长存。五楹骈列,一井鉴天。痛定思痛,倍觉国防至要;卧薪尝胆,誓缔海军摇篮。
“幸矣马限山,有缘掩藏忠骨;恸哉我子弟,何辜喋血门前!”这是何等的凄绝。辉煌可再,故人难回。下面这段悲情的表述令人忍不住掩泪:
遗恨在渊,斯水无罪。遗爱在人,斯土何愧!悲歌一曲,三江并起雄风;壮魄千秋,二潮共淘新锐……惟辉煌可再,故人难回。何日与君临流对酌,当先插柳为祭,酹月三杯!
相对而言,《鼓山赋》更考验从“抵达”转向“表达”的智商。除了赋体形式上的精雕细琢,包括对偶骈句、平仄双声押韵递转,《鼓山赋》更着意于引经据典而能化之,以钩沉旧事,激活情商。诸如:“潭填龙徙,蒙灵峤之穷经;壑隐泉喧,劳神晏之一喝”,“闽王虔心,未至而更衣罢舆;游客恣意,随缘亦净手拈香” 。
开篇一段,即以纯粹骈体把握其山川形势:
天生石鼓,地奉玉壶。雄峙左海,坐拥闽都。率九峰而迤逦,案五阜而沉浮。三江如练,岭下盘桓旋舞;二潮有约,望中吞吐自如。山雍雍兮鉴水而慧,水穆穆兮觐山而苏。
人文气息最浓的是对摩崖题刻的状写:
尔其摩崖之衔声,多书卷气息。远而观也,曾经野老布棋;近以察之,历代鸿儒走笔。隐隐兮若天风挝鼓,荡荡兮有海涛卷席。是以将军卸甲,郡守休炊。晦翁耽读,君谟忘归。赋巉岩以灵性,寓浩气于崔嵬。无价遗产,有字丰碑。剔藓摩挲,每见达人智慧;实话石说,尽抒仁者胸怀。
“天风挝鼓”“海涛卷席”带出赵汝愚和朱熹。南宋宰相赵汝愚曾两知福州,惜与在鼓山有读书处的朱熹未曾谋面。朱熹见其留下的诗中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一句,便采其中的“天风”“海涛”组成一词,亲笔书写后刻在近千米高的鼓山绝顶峰上,并留下一段惺惺相惜的佳话。 “将军卸甲”“郡守休炊”“晦翁耽读”“君谟忘归”则依次带出李甲、张伯玉、朱熹和蔡襄,分别用了典,但都不是成语,纯粹原创。就说“君谟忘归”吧,笔者不是为押韵而用上“归”字,事实上蔡襄也曾两任福州知州,在鼓山喝水岩留下摩崖题刻“忘归石”“国师岩”等,这便是明证。
《鼓山赋》是200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何立峰在达摩十八景区现场定下的创作项目,执笔者和“体现闽人精神”的主题也是在那时被确定下来的。赋文刻在“慈航架壑”景点的一块天然巨岩上。 “刻之凿凿”必先“言之凿凿”。比之“白纸黑字”,“大地艺术”更为严肃,焉敢造次?想当年,时任福州市政协主席陈扬富刚做完心脏搭桥,仍坚持徒步登山亲临现场办公会;初稿出来后,何书记亲自执笔推敲酌改,其受重视程度不亚于《闽都赋》;审定稿由原创作者以楷体全文自书后,惠安的一流石雕师傅专程赶来施工刻制。故可知闽都文化的“表达”不仅“多维”而且“难为”,辛苦是大家的,成果是共有的。
也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完成了上述的“闽都三赋”之后,笔者相继完成了《春声赋》《长乐赋》《福建师大百年赋》《华南女院百年赋》《武夷绿色丰碑赋》《福清赋》《永泰赋》《福州温泉赋》《寿山石赋》等,这些赋文多半与当地的长廊文化有关。连厦门国际园艺博览会园博苑的《杏林阁赋》、尤溪历史文化长廊卷首的《尤溪赋》等也延请笔者携“软硬两笔”双管驰援。
2005年第十五届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文联工作研讨会在福州召开。笔者手握一系列文化长廊的成功案例,实事求是地在会上作了题为“让城市公共空间文气扑面”的发言,证实文艺家在城市的文化建设中可以有所作为。
石头会说话,还会唱歌。为了让市民更真切地感受系列文化长廊所流淌的金石之声,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组织我们编纂了《闽都石语》一书,将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形象回归文本,这本书与此前出版的《闽都古韵》形成“姐妹篇”。这两部作品也被称为难得的宣传福州地域文化和城市精神的乡土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