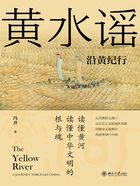
积石遐想
2019年8月
久闻积石山,梦中歌且行,而亲历积石峡口,则是近年的事了。2016年秋天到兰州,突然想到炳灵寺去,因为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古丝路的一个大节点。说奇也不奇,只要有石窟,那里必定是丝路要津,因为文化流与贸易流从来是伴生的经济地理现象。
到炳灵寺的路是条水路,从刘家峡渡口乘快艇,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一路经过黄河三峡的笔立山崖,那斑斑驳驳的山峰,其实都是古老的丹霞积石,河水从龙羊峡开始,一路延伸到这里,而处于下游几百里之外的黑山峡、红山峡和青铜峡,则是它的余脉。
下船登岸,与古来的“天下第一桥”遗址不期而遇,方才知道,为什么这炳灵寺石窟是古丝路的要津,为什么要在这里立起古丝路网的重要标识。“天下第一桥”是前秦乞伏氏时代修建的,历经风雨,自然是踪迹全无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遥想当年,车水马龙,文成公主走过,法显走过,进入西藏和新疆的无数边塞诗人也走过,而络绎不绝的商人更是鱼贯而行。据说,此桥毁于北宋与西夏交战之时,是哪一方毁桥,似无确记,但依我推断,是北宋军所为,因为党项羌人的老家在黄河一线。
炳灵寺石窟的造像始于北魏和西魏,那一尊尊面孔清秀的佛像和大大小小的供养人,明确地提示了那个繁忙的古丝路年代。人们说,从这里可以直接通向积石县,有一条狭路也显示了这一点。兰新高铁既通,这里已经不是大宗货物的必经之地,但寻常商旅依然会将这里当成必经之路。从古丝路的地理坐标来看,这里是当年的丝路主干道的交汇处,隋炀帝进入张掖和山丹,正是从这里沿着黄河和湟水,直奔祁连山的扁都口,上演了那幕西域诸侯商贾大会,为后来的盛唐气象打下了基础。
我很想从这里穿越过去,但没有适合的交通工具,也不知道怎样穿越。看完石窟,也就就此别过了,但那遗憾,一直卡在喉咙里。如今到了循化,眼看着滔滔东流的黄河水和河两岸的层层丹霞石崖,穿越的欲望再次燃起,但这次是由西向东。
在循化街头走走,街面干净利索,吃了一碗手工揪面片,味道鲜美。席间遇到两位老者,一位是藏族人,给我讲了十世班禅在这里的故居和寺庙;另一位是撒拉族人,则给我讲起撒拉族人的吃食,他不时与邻桌人插话,有的我能听懂,有的听不懂,我问是撒拉语吗,像是中亚哪个地区的语言,他说他也说不好,但听经常跑外的年轻人讲,好像与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某些发音有些一样。我知道,撒拉族的先人是中国明代时从费尔干纳盆地迁徙来的,这里还有一段白羊石的故事,所以他们的语言里,留有中亚地区人的发音尾音,也是必然的。在向他请教积石峡在哪里时,他们吃惊地笑了起来:你不知道?你现在就在积石峡镇上呀。峡上边还有积石山县,这里是积石峡的中间,走不了几里地,就是大河家,也就到了黄河的边边上。
真是有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自己也不禁笑了起来。回想来路所见,那黄河在盘山路下不断地流淌,对面河岸上山崖笔立,岩石黄中裹绿,一层层地叠加,一直顶到了蓝天上。这让我开始更加明白,积石的原本含义好像并没那么难解,也并不高古、晦涩,一切都来自眼前的山形和山貌。
在赶向大河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看如同一幅高大立扇面的积石山崖,也想起了传说中披着蓑衣卷着裤管的大禹。大禹治水的水平和思路确乎超过了他的父亲鲧,他的父亲一味用“湮”即堵塞的办法,在一般情况下或可奏效,但如果出现一连串的大雨,以及地质灾害引起的河道堰塞,不仅会淹没峡谷里的更多台地,也会造成下游毁灭性的次生灾害。大禹反其道而行之,疏通堰塞,释放了应力,也就逐步消除了黄河中上游的经常性水患源头。大禹治水并不完全是因为黄河上游阴雨连绵,或者竟如西方传说中的世界性水灾,那是发生在黄河上惊心动魄的一个连环历史场景。
环顾积石峡险峻的峡谷,谁也不会排除大禹们在积石治水的历史可能性。黄河的成长史,原本就是不断冲破湖盆和上游封闭峡谷的历史。历史总是那样的无奈,积石峡堰塞的闭塞和开通,显然是彼时解决洪水危机的一只锁钥,是慢慢打开,还是断然封闭,决定着事情后来的结局。积石山是黄河丹霞山脉和黄土高原的最初分界,从这里开始,黄河开始经过一些高低不一的峡口,进入荒漠带和黄土地带,一直流到第二个到第四个大拐弯前后的龙门和三门峡。此后的水流各有不同,需要治理的重点也不同。下游主要是如何治理泥沙造成的“悬河”,在中游则是泥沙的形成和水过峡口之后的漫流。“悬河”问题一直纠缠了上千年,即便大禹能够活得更久一点,也很难一下子找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一直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黄河上游修建了许多大水库,接着就是力推生态建设,开始摸索出解决水沙生态平衡的有效路径。就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而言,后来的太史公司马迁,将其历史功绩主要聚焦在积石和龙门两个点上,无疑还是一个有分量的历史传说判断。
历史上是否有过大禹治水应毋庸置疑,否则也就没有了夏朝的来龙去脉。即便它是一个历史符号,也是华夏民族敢于也善于与自然斗争的历史事实,体现了民族面对挑战奋斗不息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华夏民族文明发展的延续和未来。
传说中大禹治水的主要场景发生在黄河上,特别是传说密集的黄河积石峡、黄河中游的孟门和龙门(也即禹门口),此外就是黄河第四个大拐弯之后的三门峡,也涉及淮河甚至江南的一些河流。大禹是中国以家族血缘为政治纽带的王朝制度立基人,同时也是华夏民族治山治水共同品牌的创立者。大禹治水未必一定要纳入西方传说的世界大洪水一幕里,他的功业与黄河在丰雨期的河态变化直接相联,也同先民的开拓与发展节奏相一致。他的功业主要出现在尧舜禹三代相互接续的后期,这样一种连续性,也暗示着尧舜禹三代的连续存在。有关的考古成果,也提示了同样的民族历史发展逻辑。从大禹的父系传说判断,他显然出身于治水世家,而他的经《史记》认定的出生传说地汶川石纽,也提示了他崭露头角的治水第一功,最有可能在积石峡和大河家一带。
从积石镇到大河家转眼就到,这是怎样的一个小镇和小村呢?第一眼看到的是人头攒动的市场和市场尽头的黄河河面,接着就是横跨河面的一座宽大的公路梁桥。大河家顾名思义是大河的家,但门前有水路也有旱路。在这里,不由得想起了张承志的那篇《大河家》,他在文中描绘了大河家过往人物远去的历史背影,比如经历曲折的韩三十八,比如分别被称为“船客子”“走客子”“金客子”的黄河船夫、麦客和淘金的一干人众,也有旧日羊皮筏子或者小木船的惊险故事,那时这里并没有公路桥,羊皮筏子或者小木船系在固定在山崖两岸的粗铁链上,船夫伴随着惊涛骇浪冲入河心,惊险地从此岸掠到彼岸。
大河家已在甘肃省的地界,这是一个回族居民集聚镇,也是鸡鸣两省连接着甘肃永靖和青海循化、民和的地理交汇点。大河家桥是1985年建成的,船人从此永远结束了铁链飞渡黄河的历史。大河家桥西面几十米远,就是自古有名的临津渡,也叫黄河上渡或者积石渡。黄河下渡的旧址大约在东面。积石关附近有关门村,是积石峡的一个老出口和老进口,再向东,也就进入了刘家峡水库的宽阔水面。
积石关是明代设立的,但临津渡却很古老,在晋代,积石关城也被称为“白土城”。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注》中讲道:“河水又东,临津溪水注之,水自南山,北经临津城西而北流,注于河。”至少从那时起,这里就是连通炳灵寺石窟最重要的青藏丝路古渡,具有“一夫当关”之险。
这里的水流湍急,落差很大。大河家关门村正在修建一座水电站,据说竣工后发电量会超过刘家峡水电站。看来今日的积石不只是积石,更要积福。
大河家的名字叫得太霸气了,是谁在哪一年首先叫开的呢?家大河也大,毗邻的刘家峡水库更大。这里是丹霞积石的家,也是守护黄河家园的家,更是大河人一直居留的一个家。大河边有家园,大河边有市场,大河家的能量正在充分地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