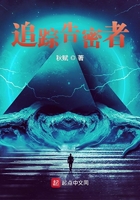
第7章 ??黑色毛衣
龙龙开着他的巡洋舰到达了帝都。
高原的烈日给他留下了黑而红的脸庞,锻打出壮硕的身材。他戴着墨镜,穿着黑色的皮衣,脖子上挂着一枚硕大的不规则的青金石,留着过肩长发,没戴毡帽,如果戴了,和当地的康巴汉子没啥区别。
那一次离家出走,香格里拉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的他,只身又去了那儿。
我一直认为他是故意的没考上大学,因为他所在的那所高中,是全市的重点学校,是百分百的高考率,百分之六十的重点大学率,因此他成了这所百年名校唯一没有考上大学的人,轰动了朝野。
临去香格里拉前,龙龙到办公室找我和张乎,要求投资他,説只要把每个月的工资,拿出三分之一给他,将来他给百分之十五的回报。
张乎説拿不出钱,但还是给了他三百元的路费。
当时私人之间的借贷流行,民间称为“抬石头”,但年利率不过百分之二,龙龙把石头抬到了这么高,我想不会是去种罂粟吧?
他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这极像了一场赌博,对方是个还不到法定年纪的孩子,你和他之间的一切都不具有法律效应,但想到或许他能成功了呢?
我答应每个月发工资时,给他一百块抬石头,至于回报也不急着,等我需要时提出钱。
他握住我的手,表示成交。
我当场把这个月的一百元股份钱给他,他写了回执,很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把箱子里的录音机拿出来送给他,这还是卡式的,虽然有点过时,但想到正好赶到香格里拉还有潮流差,还算能用上,然后又找出一堆歌带,特别舍不得地,把张学友的全部都送给了他,他感叹还是小叔叔大方,捧着一堆东西和我告别。
一年后的第一个月,他给我寄来了一千元,附了封信,説是股东分红了,我吓得不是做啥不正当的交易吧?他説是正经生意。
王科长也换上了全毛的西装,説是龙龙给买的,袖口上的商标还舍不得剪,当时部里人的孩子都是考上大学的,每每家长们在一起交流,王科长头都抬不起来,现在看来,龙龙出息最大,张乎眼红地让我问下,他还要股东不?龙龙回信,不缺股东。
所以我是最后进机关的职员,工资最低,但是靠投资了龙龙,一下子成为最有钱的人,每个月的红利,超过部长的工资,着实让人眼红。
我跟龙龙説,也别急着寄来,看把别人眼红的,汇款单整个山上都知道了,找我借钱的人开始排队,不借得罪人,借了估计也还不上,把它们再投入到生意中去,将来小叔叔养老,就全靠着它了。还特别正能量地説,有了钱就不想努力了,你小叔还想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财务自由。
到了年底,龙龙告诉我,今年分红的钱,够我在当地买套房子,问要不要把钱寄给我,我説继续生蛋吧,我住集体宿舍挺好,你王叔马上要结婚了,一间房就我一个人住,还不用花钱和打扫。
然后我问他到底投了啥?
他説起家的钱投了种植高原郁金香,听説某大学百年校庆了吗,一百万盆郁金香都是他捐赠的,现在城市建设,都想搞特色,郁金香成为香饽饽。现在开了家香格里拉城堡酒店,生意红火,将来开全国连锁,所以我的后半生就不用有啥顾虑了。
想到把钱交给他这么生财,也就开始想往着外面的世界走走了。
这是后话不提。
龙龙把自己安顿在一家熟悉的合作酒店,开车过来接我,我带着张乎的借条和密件,跟着他来到南长街的一个四合院,他安排的晚餐。
院子四周种着柿子树,从外面看就是普通的民宅,剥落的红漆大门,缺了棱角的门墩,一方青砖的壁照挡住了视线,院子是二进,外面一进养着鱼虫花草,里面一进,在正房里摆着一张桌子,龙龙介绍説店家也是与他合作的生意伙伴,他负责加工和收购香格里拉的土特产,并进行半加工,店主负责销售,我立马感觉我投入的钱,也有这里产出的一份。
桌上摆着简单的藏式火锅,一盘盘牦牛肉,各种没见过和听过的蘑菇,都是野生的,味道醇厚鲜美。
我拿出张乎给我留的东西,告诉龙龙我的任务现在开始了,我准备从中关村开始查起,想听听他的看法。
龙龙大至了解了一下案情,否定了我从中关村做起的想法,他说如果那个人还活着,他一定会上徽派菜馆对不?在帝都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定点的家乡菜地方,因此,顺着这个思路找,一定能找到。
我没想到龙龙的思路如此敏捷,他看到我在沉吟,向我介绍:
“这是梅总,老北京人,府上曾是宫廷菜的主厨,这几年藏餐火起来后,梅总也接受新的事物,专门开了这家玛吉阿米藏餐馆,梅总可以帮着打听京城所有的徽派菜馆。”
我説那一定是很多家,我们能找他们要客人的名单?那可是行业的命根子。
龙龙笑了笑説:
“小叔叔不用顾虑,等梅总调查回来,我们再想办法。
正好我也想把产业发展到帝都,您不请我,我还想自己来呢。”
龙龙这么说,是想减轻我的担忧,这孩子不知道从哪儿学的説话,情商提高了。
龙龙问我最近徽派菜馆流行吃啥?我説原来流行吃老鸭汤、十全烩菜,现在流行吃臭鳜鱼、油渣鸡毛菜,他听后问梅总能否复制,梅总説他先问问厨师,能否买到野生的鳜鱼,如果能弄到,他会开发一道比臭鳜鱼更高级的吃法。这道菜曾是项羽家宴,古代食谱里有记载。
龙龙立即把找鳜鱼的任务发到他的群中,十分钟后,他説能搞到,现在洪泽湖一带还能打到野生的,就是价格贵,梅总説,这里的客人都是要提前两周订位的,不怕价格贵,就怕没有货。
我问为什么要野生的?是味道吗?
梅总点点头又摇摇头说:
“赶明天要是有货了我试做一条,您品后再论。到时,我把四九城的爷都请来,大家来品吧。”
回到家,我拿出张呼的借条,泡了一杯茶,继续写案情分析报告,就像当年我和他在一起写调查报告一样,我给这份调查报告编了个文件号与时间,取了个文件名称:
借条秘密。
一个月后,我把师范大学讲师团的汇报材料整理完了,张乎也把图书馆的调查搞清楚了。
他给了我一份名单,上面有三个人,分别是不同系里的老师,他们共同都借过《诗抄》,从全校师生借的频率来看,这三个人借得频率最高,时间最长。
我问张乎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
“记得那八个人的名字吗?其中一人在这儿当了老师,但改了名字,所以查不到。”
我说让小海查,肯定能查到的。
他説此人去外地上的大学,户口调到外地落户了,回来后又改的名。
当时公安的电脑并没有联网,不,连电脑都没有,所以根本查不到。
我点点头,问他怎么找这三个人?
他説你来打电话联系,就説征求报告的意见,我来记录。
为了把局做得像真的一样,我让校团委的学生帮忙,做了一个横幅挂在办公桌上方,搞点气氛组的意思,方向是找名人名言之类的,学生们选了一些他们喜欢的句子,张乎勾了其中的一句: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这是马克思17岁时写在作文里的一句话。
最近我们的读书会正在攻读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当然还是张乎的商务藏书。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这是 p 大法学院研究生读的教材,难怪我们读得那么艰难。
张乎在讲解时説,这是马克思理论的逻辑底层,所以要反复通读。
第一个约来的,是美院的刘老师,我客气地问他学生参加讲师团的想法,或者説老师是不是也可以去参加?
他表现出了艺术家跳跃性的思维,问我组织上安排了哪些地方,可以让学生们去体验?
我用那点可怜巴巴的地理知识,告诉他全市有四个县,我推荐他去九华山,那里不仅风景优美,也是贫困山区,急需师资力量,这位刘老师高兴地说,累点苦点并不怕,就怕没有创作激情,然后问我有没有看过他的画?
为了有针对性的对话,我还真找了他的画册看了,我点点头,説:“刘老师的人物画得非常像,写实功力强大,眼睫毛,衣服的纤维质感,都纤毫毕现,老师这是古典主义流派吧?”
没想到他站起来,有力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大声地説:
“从现在起,我要完全抛弃写实主义风格,自从照相机发明后,就宣布了写实主义画派的死亡。你知道基弗吗?是的,就是他,画风大开大阖,画面粗犷而淋漓,下一个艺术人生,我要从学习基弗开始,颠覆自己,重新探索现实主义题材的艺术创作表现手法。”
我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不失时机地问:
“我在借书卡片上,发现您也借过《诗抄》,是不是想创作什么?”
他把长头发一甩:
“正在进行一组大型雕塑的创作,表现人类从沉睡中梦醒的瞬间状态,那是火山爆发前树木的呼吸,山崩地裂前小草的舒展,那是沉入湖底前的纵身一跃。”
“《拉奥孔》?”
正在埋头做纪录的张乎突然説了一句话,吸引了刘老师,他像打量模特那样,打量张乎那张扁平却极有辨识度的脸,特别是那两道上挑的眉尾,配合腮帮上的横肉,不怒而自威。
“阅读经典的作品,能从中激发创作欲望和爆发力。”刘老师若有所思。
我和张乎对视一眼,他放下记录的笔。
我向刘老师表示,感谢他接受我们的调查,告辞的时间到了。
他记下了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説要是九华之行落实了,一定通知他。
我们有力地握了握手,他吹了声口哨,潇洒告别。
张乎在他的名字下,打了个叉。
办公室电话响了,张乎接过电话,脸色一变,对我説,我回家一趟,等我,改为明天再约下面的两位吧。
“家里出事了吗?”我嗅出了危险的味道。
他点点头,收拾记录:
“张之的毛线背心让人抢了。”
张之不管多热的天,都在汗衫外面罩着那件用黑色的马海毛织的麻花辫子纹背心,因为张乎媳妇的悉心照顾,除了没有看住他时,会弄得满身泥污地回来,平时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人。
谁会去抢疯子的衣服,真是疯了。
不就一件背心吗,有必要这么紧张吗?眼看着名单上的人就要浮出水面,这么关键的时候离场,我表现了不理解,眉头与鼻头同时皱了。
“你不懂。”他抛下一句话就离开了。
丢下我一人冷场,独脚戏也没法唱,我赶紧找了个理由,告诉后面两位老师,校长找我们谈事,拉上校长的大旗做了张虎皮,告诉他们做好准备,明天接着来做调查。
我看着名单上剩下的一男一女,在男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勾,算是赌他是我们要找的人。
然后我在他的名字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为何吴寂寞要出卖邓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