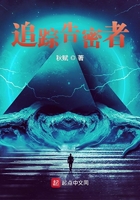
第2章 ??女贞花
我一直以为,女贞树是世界上到处都种着的树种,它是一种常绿的乔木,树干因自由地生长,通常都不是顺溜地直干,而是随着性子,长成各种各样的不直模样,你不会在W市找到一模一样的一棵女贞树,因此它们都各自带着不同的气质。
比如我办公室窗前的一排女贞树,为了与边上的棕榈树抢地盘争阳光,它们弯着身子,在空间里打着穿插,长到了二楼窗前的位置时,如同一朵绣球花那样,张开树冠,争先恐后地搬弄出白色的如米粒大的十字花,举着小伞,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一阵雨过后,台阶上、路上散满了白色的碎迷米花,一直整齐地铺到屋沿下终止。
踏着女贞花的细雨,我当时就如同走在奥斯卡的红地毯上,走到新单位报到。
学校开出的介绍信上,写着“请于下午两点钟之前到新单位准时报到。”的贴心提示。
提前了一个小时,我就走进了新单位的大门口,没想到此时还不是上班的钟点,办公楼关着门,我只能蹲在墙角,墙上挂着醒目的白底红字单位牌子,我穿着白衬衣、咖啡色的裤子,这一蹲,就象是一个惊叹号,守护着市委最重要的机关门户。
差不多蹲了半个多小时,只听得一阵木楼梯被踏响的重重落脚的声音,一个呼吸沉重的声音咳嗽了两声,唱了一句姜育恒流行歌中的一句歌词,然后两扇烟蓝色漆的百叶木门,从里面打开,一个身材壮硕、穿着一套藏青色衣裤、脸盘扁平、但眉眼清秀的年青人走了出来。
他一路走向那条碎花地毯,突然发现墙角里还蹲着一个我,扬起下巴警惕地问:
“那个人,喂,我説你呢,你蹲那干什么?想问题回家想去。这里是机关重地,中学生不要在这里玩。”
他怕是我马上就会钻进机关大门,干出点啥意外的事来,毕竟他给开的门。
这是一幢两层楼高的西班牙风格的别墅,有回廊和阳台,约有八百多平方米,原来是当地的殖民时期海关行政办公室。
W市在清朝开埠时建筑的典型样式,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证物,它盘踞在当地的一个小山头半中央,与它相邻的还有山中十多幢相同风格的建筑,可见当年的国家的殖民化程度已深入到长江下游地区。
我缓缓地站立起来,拿出手中的报到介绍信扬了扬,恭敬地説:
“老同志好,我是新来报到的学生,学校把我分配到贵单位,请老同志多多关照。”
他白了我一眼,一付不相信的样子,一把抢过介绍信,辩认着鲜红的朱色公章,对着我看了好几眼:
“站着干嘛,边上的门牌子不是写着办公室吗,敲门报到呀。还愣着干嘛,两点钟快到了。”
办公室外,乳白色的百页门分列两边,巨大的落地玻璃门关着,他走上去也不敲,扯着嗓子大声叫道:
“王主任,咱村里来新人了。”
不一会门打开了,一个刚刚从午睡状态中惊醒的精干中年人走出来,和他打了个招呼,然后示意我进屋。
从这个人的嘴里,我知道他叫张乎,之乎者也的乎。
我想怎么也不会把我分到和这么粗壮的人为同事,名字还这么虚幻。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飞机平稳地落在首都机场,还没有停好,大家第一个事就是打开手机,响起各种开机的彩铃声,然后是打开头顶柜子声音,与机舱里响起提醒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一股安全到达的浪潮涌动在四周,伴随着急着回家的脚步声和空姐最后的问候声。
因为急着回BJ,买不到经济舱,只好买了张头等舱,好处就是提前下飞机,刚一停稳,空姐邀请头等舱的客人先离开,下了飞机,一辆商务车早就停在旋梯边,不多的乘客默默地上车,只两分钟后就飞快地奔向行李大厅。
到家已是深夜时分,这趟出门准备去挑选一个喝茶的好地方,准备休息一个月,没想到路上偶遇张乎逝去的消息,于是我在第一时间回到BJ,我找到那份收藏了近二十多年的单位大信封,用瑞士小刀挑开糊得严严实实的封口,拿出了证物。
借条装在一只白色的小信封里,这么多年了,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借资没有增也没有减,张乎在写条子时,是急就的,不认真的,字迹潦草的,似有意区别与他写文章时的蝇头小楷,也仿佛是他认为将来要是出名了,不能让借钱的把柄落入我手中的有意而为之,怎么看,都不是他的笔迹,特别是乎字,几乎简化为一道弧线,闪过泛黄的信纸。
那年我急着离开原单位去BJ谋职,在离开前的一周,正在收拾办公桌时,他一直看着我,默不着声。
等我把桌上的盒子扔进垃圾箱时,他突然开口説马上单位要分配房子了,名额应是定好的,也该排到他了,会以极便宜的价格购买,他算了算还差着两千元,问我是不是能借给他度过关口?
想着去BJ安家也要花一大笔费用,但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借钱,而且是买房大业,我只好説想想办法。
当年这笔钱相当于我8个月的工资。
就是因为工资太少,所以决定下海去BJ找出路。
张乎怕我不同意,拿出了一个封好的信封,对我説:
这里面是他写下的张之回忆的资料,他知道我一直想知道当年那场深夜抓捕的事件,他早些年问出来的,他拿这些资料作为抵押。条件是如果他还不了债,我就拆开,之前不能看,他让我发誓承诺。
张之就是他发疯的大哥,他家共四个兄弟,分别是之乎者也,他居二,所以名乎。给他取名的父亲是W市重点中学的校长。
今夜我可以看了,不需再经过他的同意,想到二十多年前,花了两千元买到的故事素材,不知道是否值这个价格,或者説不知道张乎是否把知道的内容都装进了这只白色的纸糊的信封里。
想到二十多年前的谜语就要解开,是需要一番仪式感的。
先沐浴更衣,去除路途上的尘土,换上棉质的睡衣,一种本白色的老粗布缝制的出口产品,上面缝着粗大的黑色针脚,组合构成的几何型的纹路。
然后是到茶室里找茶叶,一般招待客人喜欢用红茶,大众口味,众口可调,但这会是一次较长时间费脑的追思,因此挑了一款黄茶,出自大别深山,发酵度只有百分之五,比绿茶有味,比岩茶味淡。
找到收藏在地下室的那只“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子,这么多年了还是神采依旧,一点岁月的风霜都没侵入。
水烧开蟹眼大小,停了一分钟后,提壶在手,长虹一注,完成了泡茶程序。
把书房的顶灯全部关上,只开着一盏台灯。
张乎记录的时间断断续续,从八十年代末起,大约是他进工厂当电工时,有时间和经济来源,准备着手追查当年轰动W市的这起案件。
因此记录的纸张也不相同,有企业材料入库单,有孩子的作业本纸,最后一次记载用的是原单位的文头纸,还是当年革委会的文头,不便于对外公开,发给我们当起草报告时的草稿纸用,带着方格的那种,一张纸有三百个字的方格。
粗粗地看完,这是张之在清醒状态下兄弟两人的对话,基本意思有三层:
第一层是我(张之)参与了活动,第二层是我没有出卖参与者,第三层意思是替我找到告密者。
然后是一连串的当时参与人的名字,都是用同音字标注的,明显之处是不断地划掉重写。
最近年代的一张纸,是张乎列出他找到的这些人的去向,然后在最可能的告密者的名字下面,划着圈,这其中有几个人,较为明确的是其中一个在当地师范大学教书,另一个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到了BJ经商,然后就嘎然而止。
这等于什么都没找到。这是二十多年前的资料。
我想总比一张白纸强,毕竟这是张之清醒时的回忆,现在他们兄弟二人都不在了,这桩案子是否就此划上了句号?
似乎信封里还有东西,不平整,我拎起来倒出来,一个个黑色的米粒,散发出我熟悉的微香,我仔细辨认,它们曾经是女贞花。
离开W市一路向北,再也没有看到过女贞花,原来它只生长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这是什么意思?这显然是张乎有意识放进信封里的,我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是十一粒,它诡异地象征着我们面对面在一个屋顶下度过的十一年。
那位最可能的告密者与我现在同一个城市,张乎在我奔往这座城时,就同步发起了追缴命令,以借条的形式。
无论我走向哪里,它都真实地存在着。
他深度地把我牵扯进来。
找到那位告密者,算是他还了钱。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
这是一桩怎样离奇的案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