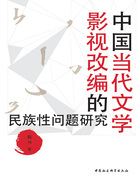
序论
本书研究内容为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文本的民族性问题。在导入正式内容之前,有必要先对民族性的概念进行辨析与界定,作为全书的理论起点与逻辑框架的依据。
汉语中的“民族性”一词在英文中对应的是“Nationality”。正如民族的概念在西方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界定,“Nationality”在英文中也有着多种含义,在《牛津英语辞典》中它的解释对应着中文的意思分别为:民族的特质或性格;民族主义或民族情感;属于一个特定民族的事实、特定国家的公民或臣民的身份;作为一个民族的分别而完整的存在、民族的独立;一个民族、一个族群团体。[1]由此可见,英文中“Nationality”可以说几乎包涵了有关民族话语的所有范畴,这个词在英语的各种具体语境下可以与Nation(民族),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性格),People(人民),Ethnic Group(族群团体)等通用。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英汉大辞典》中对其解释分别为:国籍;民族主义;独立国地位;民族性;民族风格。与牛津辞典的解释大致相同。
民族性与民族。英文中Nationality也指未建立独立国的民族,所以也对应着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汉语的“民族”是自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社会文本中,是从英文“Nation”翻译而来的,而英文“Nation”来自拉丁文,本源的意义是“生育、种族、部落”等。这个词在西方历史上经过了漫长的演变,也存在各种混乱的解释。霍布斯鲍姆认为“Nation”的现代意义是在1884年出现的,之前是指“聚居在一省、一国或一帝国境内的人群”,有时也指“外国人”[2]。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也有各种解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出版于1983年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将“民族”界定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个说法在学界比较有影响力。英国历史社会学家安东尼·D.史密斯对民族的解释比较具体详尽:“民族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被命名的人口总体,它的成员共享一块历史性的领土,拥有共同的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众性公共文化,共存于同一个经济体系,共享一套对所有成员都适用的一般性法律权利与义务。”[3]这个定义中突出了构成民族认同的几个核心要素,比如共同的神话、历史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民族的解释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4]这个解释是比较通行的,也符合汉语语境中对“民族”意义的理解,其中“共同心理素质”在徐迅看来就是“民族性格”。而共同的文化不仅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也是体现民族性的重要介质。
民族性与民族主义。在英语中,“Nationality”也有民族主义的意思。在有的学者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也经常用民族性指代民族主义。戴维·米勒《论民族性》(The Nationality)一书中,“民族性”一词即指民族主义,作者介绍说为了避免“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中的太多不确定的内涵可能会起到的误导作用,他倾向于使用“民族性”这个概念。书中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认同、民族性伦理、民族自决三个内容,其实也即“民族主义”的内容。在书中,有时民族性也指民族认同,比如他认为把民族性与其他个人认同的集体来源区分开的有五个要素:由共享信念和相互承诺构成、在历史中绵延、在特征上积极的、与特定地域相连、通过其独特的公共文化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分。[5]关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其他定义则比较繁多,比较典型的有安德森的定义:“当某一自然领土上的居民们开始感到自己在共享同一命运,有着共同的未来,或当他们感到被一种深层的同道关系联系在一起时,民族主义便产生了。”大英百科全书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是每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至高无上的世俗的忠诚”。在马克思和列宁看来,民族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6]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是先于民族的,徐迅也认为“民族主义建立了民族共同体,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这就是民族主义史。民族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它发明了‘民族’的存在,即‘臆想的共同体’。或者说,民族主义给予‘民族’以现代的定义,这个‘民族’具有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拥有优越的品质和尊严,而且承担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以‘民族’为共同体的自觉认识就是如此地被民族主义创造出来。”[7]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与民族的密切关系。并且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经常混同,因为民族国家的词汇本就是一体的。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激发了对民族的无私的爱与牺牲精神,这从一些关于母国、故乡等的词汇中可以看出来,这种纯粹的爱与牺牺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20世纪上半叶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爱国主义的倡导。
民族性与国民性、民族性格。在上述“Nationality”的英文解释中包含着“National Character”的意思,而后者在汉语中通常翻译为国民性或民族性格。而国民性批判正是中国近代以来启蒙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文化主题与任务。在中国近现代启蒙话语中,国民性一词基本指代负面的民族性格。当代社会学家沙莲香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民族性格,她的研究体系中统一使用了“民族性”一词来指代民族性格,是不带任何褒贬意义的词汇。并且她还区分了客观视角下的“国民性”与“民族性”的区别,“民族性、国民性是相对于个性的概念;国民性又是在以国家为单位考察国民特点时使用的;民族性格则相对于人格概念”[8]。当代翻译引进的国外关于民族性格研究的著作也多将National Character译为“国民性”,比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美国艾历克斯·英格尔斯所著《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一书。其中的“国民性”概念与沙莲香的“民族性”概念内涵一致,与五四话语中的“国民性”有别。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民族性”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但是在相关著作中提及的“民族性”一词显然是指National Character的意思。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将德国人的民族性和英法两国进行比较,认为“德国人是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他们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是信仰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他们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的民族性是德国因素和法国因素的混合体”。[9]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也曾经批判过唯心主义的民族论调:“满心蹉跎地将本民族放置于其他民族之上并且还幻想着其他民族能伏倒在自己面前,这纯粹是一种漫画般的、基督教的唯心主义,这只能证明它仍然深陷在德意志民族性的泥坑里。”[10]这些论述中的“民族性”与汉语中的“民族性格”接近。
民族性与民族风格。“Nationality”在英语中也有民族特质、民族风格的意思,在上述的《英汉大辞典》的释义中,就有一项是“民族风格”,而且其例句是“Nationality in art”(艺术中的民族性)。中国现当代文论和文化研究中所指的“民族性”即指文艺作品或文化的民族风格。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即是指文化的民族性,“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1]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文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是文艺的“民族性”问题。[12]
中国当代文论及当代文学评论中关于文艺的民族风格意义上的民族性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详尽了。这里民族性一般即指文艺作品体现出本民族的精神气质、伦理价值、风俗人情、审美情趣等,是本民族文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的特质,凝聚着民族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当代学者关于文学、电影民族风格/民族性问题的探讨一般有几种路径:一是评论某部具体文学或影视作品的民族风格或者某一个作家作品的民族性风格,这方面的作品比较多,不再一一列举;二是讨论一段时间内的文学或影视作品的民族性建构或民族性发展。张俊才等著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对文学的民族性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现代史上的民族文学运动及民族形式讨论进行了回溯,重点还是落在对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作品的民族性建构分别进行专章介绍,类似于作家作品论。牛运清等著的《民族性·世界性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主要是对当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及中外视野的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基本也是属于作家作品论的形式。关于影视民族性问题研究的专著有《新世纪国产电视剧的中国特色:有关中国电视剧“民族性建构”问题的探索》,对2000年以来的国产电视剧的某些类型如“主旋律”电视剧、历史剧的民族性进行个案分析并与韩剧、美剧进行对比。三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从宏观角度探讨文学、电影的民族性问题。比如王一川的《当前文学的全球民族性问题》,对“全球民族性”的概念进行阐释并具体提出了五种呈现“景观”。童庆炳的《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民族性和开放性之间》,指出了文化进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提出了“开放型的民族性”文化立场。金丹元、赵辉的《全球化与民族性:关于电影的审美思考》,指出中国电影美学中的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文化审美的强大生命力,在应对好莱坞式的全球化挑战中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所指的“民族性”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即包括上述英文“Nationality”所对应的大部分含义:民族主义、民族性格、民族风格等,也包括从这几个含义中引申出来的相关的民族性主题,包括民族精神、民族认同等,而不单单是聚焦于中国传统文论指涉的民族形式、民族审美等狭义的“民族性”范畴。因为笔者认为这样一个宽泛的“民族性”框架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段时间内民族文艺与“民族”相关的所有内涵。实际上,不同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下文艺作品与民族国家的互动是一个非常复杂微妙的过程,单一的“民族性”释义难以穷尽其繁复与幽微,需要从“民族性”的多义背景下进行多维透视。所以解码这一复杂的互动关系仅靠传统的文艺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支撑,这些理论将构成本书的主要理论支撑。
在将“民族性”研究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拓展之后,本书还试图将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是当代小说)与当代电影进行关联,不再单一、孤立地审视文学或影视的民族性问题,而是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以“民族性”为主线来进行宏观的审视,通过改编这一线索,来审视不同媒介、不同创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文化语境下,小说源文本的民族性是如何在其影视互文本中发生迁移流转的。这也是本书对上述当代文学、影视已有民族性研究的一个突破。
当代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关联实际上是非常密切的,可以说互为“互文本”,彼此指涉,互相成就。这个关联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的影视改编。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就经常取材于文学资源,或改编自现代文学经典,或改编自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十七年”的革命文学作品不仅是当时电影的重要改编文本,而且是其他媒介文艺形式的重要来源,并且在新时期以后被不断翻拍,成为重要的影视IP。其中,红色经典“抗战”小说得以跨时代、跨媒介改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民族性特色,包括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新时期以后,当代文学的影视改编依然是高潮不断,20世纪80年代文化反思、文化寻根语境下,当代文学在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过程中,仍然有一条“民族性”主线清晰可见,有的导演借助诗意小说或民俗小说的改编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理解与认同,比如吴贻弓的《城南旧事》、谢晋的《芙蓉镇》等都是改编自同名小说,表现了传统文化的审美意境。而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如吴天明、陈凯歌、张艺谋等则借助西部文学发力,通过一系列改编电影表达了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认同与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小说改编逐渐形成热潮,代表性作品就是二月河的清史系列小说的改编。新世纪以来,历史剧上映的热度几乎一直没有消减过,革命历史剧与古装历史剧交相辉映,轮流展演,其中很多革命历史剧是改编自“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或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历史小说,而古装历史剧则都是由当红网络小说改编而来。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历史影视剧都是对民族历史发展、民族历史生活及民族历史人物的艺术再现,而拥有共同的历史与祖先、共同的英雄神话传说恰是形成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在历史小说及由其改编的历史影视剧中渗透的历史精神、民族文化也与民族性问题密切相关。值得提及的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小说或者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小说也有许多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姜戎的《狼图腾》都是在当时引起过轰动的作品,前者被汉族导演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后者被法国导演改编为电影。首先,少数民族文艺作品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民族艺术风格也是中华民族性的有机成分。其次,文本在经过不同族群的导演演绎之后其中所体现的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与此相似的是跨国“离散”作家的作品改编,比如张翎、严歌苓的小说。后者的作品尤其受导演偏爱,多数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但是跨国族作家的身份认同必然与本土导演的身份认同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改编过程中,也存着如上面少数民族作品改编一样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迁移问题。最后,作为不同的媒介形式,它们的受众群体也有差异,小说与电影、电视两种文艺形式所体现的民族审美心理、审美情趣在具有共性之外,还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因为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不同,这种差异也会更明显,所以从民族艺术风格上去探讨当代小说与其改编影视剧之间的异同也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
立足民族性问题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影视改编,也是本书对当代文学影视改编研究的一个创新之处。文学的电影改编,历来是研究的热点。一般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理论上探讨改编技巧、两种艺术的美学差异等,二是针对具体作品改编进行比较分析。从理论建树上看,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已经比较成熟,代表性的理论家有美国的乔治·布鲁斯东,罗伯特·斯塔姆,琳达·柯斯坦滋卡希尔,法国的安德烈·巴赞等,他们的主要理论建树有:1.总结了从文学转变为电影的几种模式,比如琳达在《电影中的文学》一书中指出,从文学到电影有三种翻译方式:文学的翻译——尽可能地接近原著;传统的翻译——保留原著的一切特色,但会更新电影制作者视为必需的细节;激进的翻译——用极端和革命的方式重构原著,使电影成为一项独立的作品。安德烈·巴赞在《非纯电影辩——为改编辩护》一文中也有近似的分类。2.分析了电影和文学原著之间在叙述和美学上的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除此之外,他们对世界经典电影及其文学原著也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
国内学术界对当代文学影视改编的研究近几年由于研究对象的不断丰富而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对当代文学电影改编的叙事问题包括视角、节奏、修辞等进行全面的论述,如陈林侠所著的《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孙柏所著的《摆渡的场景:从文学到电影》,赵庆超所著的《文学书写的影像转身——中国新时期电影改编研究》等对该问题都有涉及。2.分析电影改编的社会语境及文本本身的文化内涵。如傅明根的《从文学到电影——第五代电影改编研究》,分析了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中的意识形态内涵。上述陈林侠的著作对当代改编电影中表现出来的“物欲”“权欲”“情欲”等主题进行了文化学的批评。3.对某一类型文学或单一文本的影视改编进行比较分析。如王宗峰所著的《凡圣之维: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跨媒介研究》主要论述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两次影视改编的社会背景及其“卡里斯马”系统的变迁。姚丹的《“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对小说《林海雪原》及其后来的改编文本生成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审美特征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史料翔实。张颐武的《共同的想象 共同的追寻》一文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小说与电影的互动关系。周政保的《张艺谋的艺术观——从小说到电影》一文分析了由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中体现出来的导演张艺谋的审美选择和艺术个性。此外较多的文章是针对某部影片与原著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
综上所述,已有的相关研究为本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参照视野。但目前关于当代文学影视改编的研究中尚未有对文学文本与影视改编文本的民族性问题进行全面系统阐释的,所以聚焦民族性问题,将是本书对当代文学影视改编研究的一个突破。此外,由于学者关注的视点不同,涉及的改编样本偏于某一类型,对文学改编电视剧关注不够,不能反映中国当代文学影视改编的全貌,本书不仅将文学的电影改编文本纳入研究视野,而且将其电视剧文本也同样进行比较分析,比如小说《红高粱家族》的互文本既有电影《红高粱》,也有电视剧《红高粱》,小说《金陵十三钗》既有电影互文本,也有电视剧互文本,同样,红色经典抗战小说既有电影互文本,新时期以后更多的是其电视剧互文本,比如小说《敌后武工队》,不仅有电影版本,新时期以后还存在多个电视剧版本,长期以来,这些作品的电视剧文本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所以将当代文学原著所有的电视剧版本也完全纳入研究视域中,也是本书对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领域的一点贡献。
如上所述,本书的主题是广义的“民族性”问题,所以本书在对文学及其影视文本进行分析的时候,重点不在改编艺术及改编过程的研究上,而是对不同媒介文本呈现的“民族性”内涵进行分析,以探究媒介形式、创作者理念、时代文化思潮对文艺作品民族性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的影响。同样,本书的逻辑主线也是“民族性”主题的不同层面,以主题来划分章节,同一主题下,可能会汇集当代不同时期的作品。在每一章中,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会有文本变迁的时间线索。比如,红色经典“抗战”小说及其不同的影视互文本之间就有着较大的时代差异,按照民族主义的主题框架来收纳这些作品,同时在这一大框架下再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小说与影视文本中的民族主义异同,可能更有利于体现本书“民族性”研究的主旨,有利于逻辑主线的凸显。在研究文本的选择上,本书同样以鲜明的“民族性”内涵与形式作为选择标准,所以有些当下的都市题材作品未能进入本书的研究范围,当然由于本人精力有限,可能存在遗漏部分代表性作品的现象。
本书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编 民族主义:当代“抗战”题材小说的影视改编。
本编聚集“抗战”题材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探寻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在文艺作品中的呈现。本编以红色经典“抗战”小说的影视改编为主体,阐述了从源文本到改编文本一脉相承的民族国家意识,即家国思想、乡土情结以及“同仇敌忾”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此外,通过“乡绅叙事”与“女性叙事”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比较原著小说与由其改编的影视剧由于时代差异及媒介差异而表现出民族性叙事的微妙变迁。而红色经典“抗战”题材小说较之后来的影视剧文本在艺术上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其现实主义手法,从而使其具有了社会史的意义。这些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对现代化转型中的农业中国的政治经济及伦理文化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揭示了“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广大农民在战争的苦难中接受党的宣传教育并受惠于根据地的民生政策,克服了文化因袭的重荷,有了明晰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了坚定的抵抗精神,成为抗战胜利及后来革命最终胜利的坚实基础。而这些,恰恰是当下作为娱乐文本的“抗日神剧”所缺失的。本编还包括新时期以后的一些属于“新历史”范畴的抗战题材小说的电视改编,包括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尤凤伟小说《生存》的影视改变,分析小说的生命、生存主题是如何演变为民族性主题的。
第二编 民族历史: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影视改编。
本编立足民族历史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以几部清史题材小说的影视改编为样本,分析凌力与二月河历史书写中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雅”与“俗”的风格区分,以及这种风格区分与时代思潮的脉动关系;通过上述两位作家作品的影视改编文本,分析历史影视剧在呈现民族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宫斗剧对权谋文化的渲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歪曲等。这些问题是不利于表现民族文化的正面积极因素,从而不利于民族认同的形成的;以“悲剧精神”为切入点,分析革命历史小说影视改编版本的历史意识问题,即变历史悲剧为喜剧的创作倾向。这种倾向使民族英雄的形象从崇高变为诙谐,将复杂的历史冲突简单化、娱乐化,不利于民族历史的真实呈现和民族情感的凝聚、民族反思精神的形成。
第三编 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跨族群写作的影视改编。
本编主要探讨跨族群写作及其影视改编作品中民族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异同。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海外华人、香港作家及境内跨族群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及其影视改编作品,以分析基于不同的混杂的文化身份与地位而导致的文化认同的差异。在小说文本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症候”,在改编的影视剧中得到解决之道,即:以中华文化为主体认同,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准则,以血缘亲情为凝聚力,以“团圆”“和合”精神来迎接“游子”归来,构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自信。同时,跨族群写作的小说与改编的影视剧相比,能够具有跨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具有一定程度“超然物外”的客观性,从而在文化呈现上具有深度与维度。第二部分则探讨另一种跨族群写作的影视改编的民族性,即由纯粹的汉族作家写作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而这些作品在被改编成为影视剧后,由于影视导演的民族身份与小说作者又有差异,所以不同的文本又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与文化认同。
第四编 中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及国家形象构建:西部文学的影视改编。
本编拟选取西部文学及其影视改编文本来研究其中体现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本文聚焦的西部文学范围兼顾地理与文化概念,主要是西北黄河流域一带包括陕西、山西的一部分反映民族精神、反思民族文化的作品,以及一些在地理上虽然不是严格西部的小说,但却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及民族文化色彩,同时被改编成影视后地域发生挪移变为“西部”的作品。比如《老井》《黄土地》《平凡的世界》《百鸟朝凤》等作品。这些作品全面客观地表现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全息图谱,包括:勤劳节俭;韧、忍与抗争性;固土重迁与流动性;保守与创新;要面子与自私;家族本位;乐天知命。当然,在文学原著与改编文本之间在民族性格的表现上还是略有差异的。本编也将分析这种差异。
从上述西部文学及影视对民族性格全面、动态、客观的展示中,我们可以把握到其中正面、积极的因素,这些因素恰是与我们民族精神重合与同构的。总体而言,西部文艺作品对中华民族性的表现是在肯定与认同的基础上进行反思的,体现了创作者对民族、人民、土地的深情。这种正面、积极的国民性格的塑造有利于树立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本编也将分析国民性格与国家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从而探讨上述文艺作品尤其是改编影视剧对外传播积极国家形象的意义。
第五编 民族审美心理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电影改编。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审美心理结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比如追求和谐与圆满的审美情感,重直觉、意象的审美思维方式,“神游物外”的浪漫主义想象等。本编试图探究上述中华民族审美心理是如何在当代文学作品向影视作品转换的过程中发生作用的,也即在影视文本与原著文本之间艺术表现形式的差异有多大程度是受到民族审美心理影响的。本编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中和”精神影响下影视剧的“大团圆结局”。这种结局与原著的悲剧结局有明显区别,有的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文化理想与价值追求,从而具有抚慰心灵、平衡情感的意义,比如一些反映亲情和睦、家庭团圆的属于伦理范畴的大团圆结局。有的则是掩盖矛盾、回避问题,缺乏反思精神。第二是分析“天人合一”思想与电影中的“意境”与“仪式”。电影在创造意境和仪式感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所以在当代文学的电影改编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电影较之原著具有鲜明的意境建构或仪式感,表现出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第三是分析“抗日神剧”在民族传奇故事影响下的浪漫主义风格,从民族审美心理的角度探究严肃的写实的抗战题材文学是如何在当下演变为“抗日神剧”的。
结语 中国当代文学影视改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本部分是全书内容的总结,立足文艺作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关系,梳理了当代文学及其影视改编文本的民族性构建历史,从而发见文艺作品的民族性既有传承性,又体现当代性;在部分作品的影视改编中,有的由于创作者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焦虑”,在民族性构建方面出现了误区,有的则是表现了传统文化中负面的内容,不能体现民族性的时代特色,所以文艺作品要坚守民族本位、表现文化自信,同时要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引导受众审美心理与时俱进。此外,当代文学的影视改编过程中也体现了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密切关系,当代文学通过影视改编走向世界并获得广泛声誉的多是原著或电影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体现了普遍的人类情怀与价值,具有世界意义、人类意义的。在全球化和多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文学和电影可以互相借鉴、互相提升,构建积极的民族形象,并实现有影响力的国际传播,为文化强国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1]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2] 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3] [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4] 转引自徐迅《民族主义》,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5] 参见[英]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6] 以上定义参见徐迅《民族主义》,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46—48页。
[7] 徐迅:《民族主义》,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8]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9] 转引自陈锐《马克思主义对德国民族性的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
[10] 转引自安宝洋《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性思想及其时代价值》,《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11期。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12]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 com/politics/2016-11/30/c_11200253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