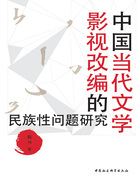
第三节 从小说到影视:“乡绅”形象的衍变
在关于中国当代红色经典“抗战”小说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其中的“乡绅”阶层形象一直没有得到关注。然而这个阶层的人物在小说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体现了抗战时期乡土社会阶层变迁的重要信息,也反映了民族主义话语、阶级斗争话语对乡土社会的重要影响。本节拟透过小说中这个阶层人物在抗战时的没落与失语,来透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是如何在民族危机时代,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生巨变的,同时,通过分析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中的乡绅形象较之原著的变化,反映时代文化语境对文艺作品中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基于血缘伦理、由乡村权威控制的自治组织,在“天高皇帝远”的底层乡村,由宗族长和乡绅组成的“合法性权威”得到社区民众的普遍尊重和认可,在社区事务的处理中有着比政治权力还要有效的控制功能,起着维护社区稳定平衡、保持文化传承的作用。从广义的范围上讲,20世纪上半纪的乡绅作为乡土社会的精神领袖,主要包括“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友”“受过教育的地主”[43],“旧式功名持有者”“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乡村教师”“有势力的家族长”等[44]。其合法性权威的奠定主要靠自身的德高望重和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尽责,经济条件倒是一个次要的因素。乡绅在乡村社会中的主要任务有:作为社区的社会领袖和代表,担当地方的警备力量,调解人民日常的纠纷,关心社区的灾荒、赈济、时疫等,为社区的民众树立楷模[45]。
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勃兴造成了20世纪乡绅阶层的第一次分化和流动。大批乡绅失去了传统的晋升渠道从而流向新的社会职业阶层,有的开始离开乡土走向城市[46]。抗战爆发前后直至抗战胜利,由于乡土社会的剧烈变动,乡绅阶层进一步分化。“作为个体的人,他的阶级属性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阶级结构的稳定性不在于个体的固定不变,而恰恰在于个体的流动性,结构震荡剧烈时尤为如此。抗战时期诸多因素促使根据地各社会阶级处于不断流动之中,地主、富家阶级普遍衰落,贫雇农阶级处于上升之中。”[47]另一方面,由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策的实施、群众运动的开展及无产阶级抗战英雄形象的树立宣传,乡绅在乡土社会精神领袖的权威地位进一步下滑乃至被后者全面取代,从此以后,基本退出了乡村公共事务的权力话语系统。
从红色经典“抗战”题材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出乡绅的分化和没落。组织力量抵抗外敌、救济同胞、保护乡土应该是传统乡绅义不容辞的社区公共责任。然而,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乡绅阶层,在面临民族危机时,有的顽固投敌,有的左右摇摆,有的虽然在受到教育后醒悟,但基本都失去了挺身而出、守望乡土、积极有为的担当和责任,在国难当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抗战大潮中,注定要丧失在乡土社会中的主流话语地位,被新的权威——关注民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发动和组织农民、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人所取代。
出现在这些小说中的乡绅由于各自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在对待抗日工作的具体态度上,还是有分化差异的。第一类是大地主兼资本家且同国民党政府有关联的,都是反对并破坏抗日工作的,属于劣绅兼汉奸。第二类是中小地主,或投敌作汉奸,或左右摇摆求周全。第三类是一些财力微薄,在乡土社会声望的获得主要是靠宗族地位、人品、学识的乡绅,则有可能在现实危机的教育下同情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战工作,并保持民族大义。小说叙述者对前两类乡绅在抗日大潮中的表现都持一种讽刺、谴责和高度怀疑的态度,这种讽刺和怀疑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小说中普遍出现的人物在乡村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言行矛盾。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乡村或村落公共空间概念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但又不完全相同,它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例如,在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戏台、祠堂、集市,甚至水井附近、小河边、场院、碾盘周围,人们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二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例如,村落内的企业组织、乡村文艺活动、村民集会、红白喜事仪式活动,人们同样可以在其中进行交流、交往。”[48]这样的乡村公共空间在抗战时期同样存在,成为战时宣传动员或信息交流的重要舆论场所。
《平原枪声》中全县最大的地主苏金荣,不仅在乡下广有土地,还离开乡土,在天津汉口都有生意,同时在外边结识了不少官僚士绅,可以说拥有乡绅阶层影响力来源的财富和人脉。也正因为他的经济地位并同国民党官员刘中正的勾结,而成为顽固反共的汉奸。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全县各界人士抗日动员大会上,县委副书记杜平以‘战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报告了苏金荣捐枪的消息,当场就有不少士绅、地主响应,自动报出捐献枪支的数字。这一来弄得苏金荣哭笑不得,不过他还是冠冕堂皇地讲了一通抗日的主张,可是当他一回到他的公馆,脸色就勃然大变,破口痛骂起来。”[49]这里的“抗日动员大会”是战时乡土社会常见的公共空间,与后来的农民诉苦大会一样,是乡土舆论表达的空间。而苏金荣的公馆则是一个私人空间,人物在这两个地方的表现是迥然不同的。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接近历史叙述。在村庄遇到灾荒、战乱时捐款、捐粮既体现乡绅的权威,也是职责所在。所以相关史料记载中,常见士绅赈灾或进行“救国捐”的行为。比如《河南全民抗战》一书中记载,1942年河南遇日军侵略又逢大灾时,“各县绅商纷纷捐粮、捐款,救助灾贫。继1942年底临汝县周筱山献粮40石后,许昌周锦堂捐款17万元……全县因捐助灾贫受到政府各种奖励的达12685人。”[50]又如《晋城抗战史》记载:“中共沁水县工委、县政府、县牺盟会为解决新军和自卫队发展壮大后经费不足的问题,派出干部深入各区、村,发动群众,摸底劝捐……县委组织委员苏平(女)多次登门说服第四区良平大财主苏贯生,使其一次捐出了银元4000元……这笔救国捐,为解决财政困难、支持新军起了很大的作用”[51]。历史叙述中可见的仅是客观的数字及公共空间的语言、行动,而文学叙述则可以深入人物内心和私人空间,可以表达叙述者的主观倾向。所以就有了上述文字中揭露苏金荣心态的“哭笑不得”“冠冕堂皇”等主观色彩鲜明的词语及对其在自家公馆表现的描写。
与苏金荣相同,《苦菜花》中的王柬之也是一个典型的出身大地主阶级、离开乡土之后结交国民党的乡绅,在北平的大学里读过书,有新学背景,在城里教过书,然后回乡兴办公学,实际身份则是潜伏的汉奸特务。他在家乡的公共场所当着乡人的面说过自己的见闻和遭遇:“国民党如何不抗战,鬼子来了,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祖国遍地一片焦土。同胞的血淋淋的尸首使他认请了现实,深深感到亡国奴的日子没法过下去,他领着学生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结果被敌人抓去关在牢狱里好几个月,出来他又不顾迫害地参加了救亡工作……当他听说家乡有了共产党领导抗日,就不顾敌人的阻难而奔回来,誓为抗日尽力。他说这些话时,那种痛苦万状、捧腹揪心的神态,很使人们动心。光说空话不行,王柬之还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抗日爱国心。他把山峦、土地献出一部分来,又把大批陈粮交了公粮,并自愿帮助政府办小学,以尽他知识分子一点力量。”[52]随后,叙述者马上就将画面切换到王家家宴这个私人场景,王柬之和几个同党一起饮酒,人物的语言和心里活动中充满了对穷人的仇恨。在这些叙述中,同样存在着上述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矛盾。
《敌后武工队》中的地主周敬山属于扎根乡土的土财主,有几门亲戚在官面上,有着乡绅的经济地位和人脉资源,所以“他在村里说句话,出个主意,都像板上钉了钉……村里的地主和富农,大多看他眼色行事”[53]。此人是典型的中间人物,摇摆于各方势力之间,虽没有沦为汉奸,但是出于个人私利,对减租减息和抗日工作不积极。在他家召开的一次由武工队主持的集会上,大小地主、债户集聚一堂,显然也构成一个公共领域,周敬山“跳上炕,像心甘情愿的样子:‘乡亲们,老少爷们。在咱村人都称我是首户,首户干什么也不能走在后面。抗日政府为了把鬼子早日打出去,让胜利早日到来,要发展生产。生产必得人干。要是咱有钱的不为穷苦点的人们想,他们自然不好好生产,所以就颁发了减租减息法令,这个我从心眼里拥护,要减就先从我这来”[54]。其他地主一看他表态了,也都纷纷响应。在这个场景之前、之后,叙述者用了大量的篇幅交代周敬山对武工队领导的工作反感、抵触同时又惧怕的复杂内心活动,与前面公共领域的“心甘情愿”的表现形成矛盾。
小说中反映的前两类地主乡绅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矛盾,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复杂统战局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党对地主阶级既争取联合又怀疑斗争的矛盾态度。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发表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作为中间势力中的开明绅士虽然“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55]而顽固势力中的抗日派也可能会对我们采取两面政策,我们对付他们的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就是“以斗争求团结”[56]。小说《苦菜花》中的共产党员姜永泉在王柬芝还没有暴露前一直对他心存怀疑:“是什么力量使王柬芝和这个汉奸家庭的关系割裂得一干二净呢!是真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明大理,敌人的惨无人道的兽行激发起他爱国的热情吗?可惜没法了解这个人在外面的经历。是啊,娟子、德松他们说的也有理,他终究是个财主,很难真心跟我们一道走。对,要团结他抗日,也要防备他存心不良。”[57]姜永泉的这一心理活动正体现了上述党对地主阶级抗日意图及表现的怀疑和两面策略。
红色经典“抗战”小说的叙述者对第三类乡绅的态度表现得比较复杂,既肯定其由传统因袭或自身品行树立的在乡民中的影响力,又要批判其反现代性的“依托乡土”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既肯定其基于传统“家国思想”的民族气节,又批评其因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缺失而带来的对抗日工作认识上的局限,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导致他们缺少行动上的执行力或意志的坚定性,所以仍然不能承担传统乡绅组织力量守卫乡土的公共责任,不能成为抗战时期乡土社会的精神领袖。和前两类经常处于矛盾话语中的乡绅不同,这一类乡绅则多数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转变过程中。这一类乡绅还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类:
拥有宗法权威的家族族长。《苦菜花》中的四大爷是令娟子母亲非常畏惧的大家族的族长,恪守封建传统道德,反对妇女参加革命组织,鬼子进村的时候也坚决不撤退,认为鬼子是冲共产党来的,和自己没关系,只有当经受了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才开始转变观念,并支持儿子参军抗日。
参与乡村基层旧政权的士绅。自晚清以来直至20世纪30年代,乡村自治的基层政权中吸纳了一些本地有声望、有文化、有经济基础的人加入,担任乡长、村长、村副或庄长等,这些人往往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在红色经典“抗战”小说中,出现了一些中农以下的村长或村副形象,他们虽然不是抗日的主要力量,起初也有软弱胆小的一面,甚至违心地担任一些伪职,但因为有基本的道德感、民族意识和对村民的责任感,所以在经过残酷斗争或共产党的争取教育之后,最后都能站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有的甚至壮烈牺牲。比如《苦菜花》中村长老德顺阅历广,应酬过各色人等,胆小怕事,“缺乏共产党教导出来的青年人那种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还留恋他那虽不富裕却习惯了的小家庭生活”[58]。但是目睹了日寇残害乡人的场景后,他觉醒了,“他像父亲般地目睹孩子的死,看着鲜血染红了的沙河。这是那些鬼子和汉奸在随意杀害自己的亲人。他瞅着敌人那股疯狂残暴劲,心里涌上来的愤恨,驱逐了恐怖,他全身被复仇的火焰烧炙着”[59]。最后在现场和敌人搏斗牺牲了。支撑老德顺和日寇搏斗的爱护乡人的“父亲式”情感其实就是乡绅对乡民的义务感和伦理情。这类人物还有《吕梁英雄传》中汉家山的伪村副郝秀成,出身中农,因为有文化且乐于帮助村人在村里威望很高,虽然在日本人威胁下作了村副,但他看过很多历史古书,“知道从古至今亡国的痛苦”[60],因此应付着伪差,暗中保护乡人,后来在八路军的策反下参加了锄奸行动,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来自旧学体系的乡村文人。这类人接受过科举考试的训练,饱读诗书,通晓儒家文化礼仪。“中国文字难以掌握,阻碍了劳动阶级识字读书,只有那些能以读书消磨安闲岁月的人,才有掌握中国经典的希望;掌握了这些经典,他们就成了通晓传统道德礼教的人。一个主要依靠传统礼制治理的社会对于懂得礼教的人给予崇高的威望。”[61]因为“与文字、礼仪有关的各种知识在村民的生活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62],所以拥有文化资本、服务社区文化事务的乡村文人在村中有着较高的地位也是情理之中。《吕梁英雄传》中的“二先生”老秀才白文魁显然属于这一类人物,其衣着言行都符合其文化身份和社区文化功能。他穿的是“大襟长袖的古式袄子,配着顶半新不旧的黑市布瓜壳帽,腿上扎着腿带,胸脯上常年挂着挑牙签子,上面拴个一寸大小的胡梳。闲下无事时,戴起铜边老花眼镜,一面看木版古书,一面使用这小胡梳”[63]。他在乡村获得威望的原因主要是人品及文化以及建立这二者基础上的调解乡里纷争、发动救济的功能:“因为他为人正直,在村里能说几句公道话,又有点学问,说话爱嚼字眼,往年间村里人买地写约,说合调解,一定请他来当个中人。”[64]当日本人入侵康家寨后,二先生仍能保持士人洁身自好的品质,不愿让女儿嫁有权势的汉奸、密谍组长;一定限度内也能起到发动村民的作用,比如当汉奸假日本人名义要债逼死村民后,村人都征询他意见,他倡导大家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然而其影响力也就仅限于此了,他不是康家寨抗日斗争的中坚分子,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仍属于被解救的人物,自家女儿被强娶的麻烦还是依靠村里共产党领导下的民兵解决的。
《平原枪声》中的马宝堂也属于这类人物,他中过秀才,然后回乡教书。因为马庄没有财主,所以有文化的马宝堂就成了村里“唯一有地位的人”,自信连劣绅苏金荣也不能怎么样他。基于传统文人的爱国思想,抗战爆发后,他在村里的文化功能仍然存在,只不过开始转变为服务抗日、宣传抗日,为村人写了几十年春联的马宝堂开始热衷于写宣传抗日的报头,在关帝庙这样一个农民闲时集会的场所,他成了议论国事的主要角色。最后在面对汉奸和日寇逼问八路军去向时,马宝堂坚守住了士大夫的气节壮烈牺牲。然而这样一个为抗日牺牲的士绅在叙述者笔下仍然是被改造、被转变的失落的形象:他起初思想守旧,认为共产党不正统,对蒋介石的中央军高度评价,经受了中央军对村民的哄抢和打骂后马宝堂对国民党失望了,当他伤好后,又发现其在关帝庙的话语地位又被新兴的党的抗日力量取代了:“村里组织了农会、儿童团,肖家区还组织了游击队,宣传讲演,减租减息,男女老少,个个忙碌,再不像在关帝庙前听他谈论‘腰别子’那种神情了。”[65]这时的他终于明白了:“抗日只有跟着共产党走”。[66]当然,叙述者本着尊重史实的态度,并没有让这个开明士绅变成共产党人,所以最后他的牺牲场景也有别于后者,仍然是基于乡绅的文化信念和乡土情结的牺牲。面对汉奸的劝诱,他想的是气节:“我堂堂正人君子,怎么能卖主求荣。一死有之,岂能惧哉!”[67]鬼子对乡民的残害激发了他的怒火,基于对乡人的爱护和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自我牺牲,其时在他脑海中盘旋的也都是岳飞、戚继光、郑成功这些传统爱国人物形象。
20世纪60年代改编的电影由于处于与小说同样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历史语境中,在乡绅形象的塑造上基本和原著保持了一致,甚至第一类乡绅的反动投敌及道德败坏的一面比原著还要强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时代语境的变迁及国共两党关系的和缓及中共对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承认,呈现在影视中的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第一类乡绅形象及其民族立场开始产生或微妙或显著的变化。有的从小说中主要反派人物的地位变为无足轻重的角色,比如2001年的电影《平原枪声》中的苏金荣在电影开始不久,因为中共施行的反间计,就被日本人枪杀了,所以在电影中基本没有表现出作恶和投敌的一面,对马英更没有如小说中所述的强奸其姐这样的家仇,反倒像一个无奈的被时代裹挟的背运的土地主。这和原著中那个被高度怀疑和否定的主要反面人物苏金荣有明显区别。同样,在2010年的电视剧中,苏金荣也没有和马英的家仇和血债,身上有了小说中不明显的封建家长的气质,在第3集就被手下杨百顺暗杀,所以也不是剧中主要的反面人物。而且剧中还通过人物语言揭示了其做汉奸的动机:“国难当头,要么跟着国军一路溃败,要么被共产党分田分地,家破人亡,只有跟日本人这条路。”国难当头,是时代背景,避免家破人亡,也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这段话里,也有许多的无奈,和小说中苏金荣主动积极地反共投日是有区别的。
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类中的反动乡绅,有的虽然仍是主要反面人物,但也不再是顽固反动、坚决投敌、穷凶极恶的,而是有着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表现出原著中没有的善恶之念的挣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向善的心理和行为。比如2004年上映的电视连续剧《苦菜花》中的王柬之,虽然最终身份和原著一样,是隐藏的汉奸,但剧中王柬之的人生和心路历程和小说中完全不同,因而和其他人物的关系也与小说迥然不同。剧中刚出场时的王柬之是一个地主家庭的叛逆者形象,他同情以“母亲”为代表的家中下人,反抗包办婚姻,并在夜里准备和“母亲”私奔逃离家庭。这和小说中那个坚决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暗中维护家庭利益的王柬之的起点已是不同。同时,由于和“母亲”的这段交情,使得小说中两者间势不两立的血海深仇变成了脉脉温情,阶级对立的界线被人情融化,所以在剧中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是相信和感恩王柬之的,甚至也影响到了姜永泉对他的态度。和小说中对王柬之始终保持高度怀疑的姜永泉不同,剧中的姜永泉还劝对王家有看法的娟子“做人得懂个理儿,知恩图报,以心待人”,要她理解母亲对王柬之的感情。由于不同文本中“母亲”的性格不同及王柬之与“母亲”的不同关系,王柬之的最终命运也是不同的。小说中母亲还保留着女性的、母性的很多气质,和王柬之并没有很多的直接冲突。电影中的“母亲”阶级性压倒了母性,所以最后是王柬之跑到了“母亲”家的院里,被“母亲”亲手枪毙的。而电视剧中的“母亲”则对王柬之始终存有复杂的情感,最后是王柬之撞墙自杀的悲情场面。这样一个与原著和20世纪60年代电影差异很大的结局,反映了编导对小说中顽固乡绅的某种程度上的同情和理解,也反映了新时期以后阶级性与民族性的逐渐松绑,也即不再简单以阶级立场来判定民族立场,大地主阶级不一定全部是死心塌地卖国投敌的,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复杂性。
同样,小说中第二类左右摇摆型乡绅在新时期的影视剧中也开始转型为政治进步、有民族立场的开明士绅。比如2005年电视连续剧《敌后武工队》中的周大拿,刚出场时接近小说原型,是村中的第一大户,对中共的减租减息不积极,但他离家多年担任八路军排长的儿子给他来了一封信,信中表示要先尽忠才能尽孝,认为八路军才是真正地爱百姓爱国。此信从传统人伦切入到政治主题和民族大义,打动了周大拿,他对下人控诉了日本人的罪恶,表示儿子是八路的人,等于他也是八路的人。他后来的壮烈牺牲也体现出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小说中自私自利、没有抗日意识的周大拿大相径庭。
小说中第三类乡绅有的在影视剧中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从被教育和改造的士绅转变为立场始终坚定,有胆有识的革命者,从小说中被争取的角色变为值得依靠的抗日力量。2004年电视剧《吕梁英雄传》中的主要人物和情节基本尊重原著,变化不太,但二先生的形象却和原著有了分野。小说中的二先生虽然能一定程度上承担乡绅对村民救济的责任,依靠学识和人品获得乡村声望,但却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如同其他村民一样,有软弱怕事的一面,比如面对地痞流氓对其女的抢亲,二先生慌慌张张,甚至是哭着向民兵求救。而电视剧中的二先生则是非常镇定勇敢地直接拒绝了皇协军大队长邱得世的求婚。小说中的二先生因为经济状况较好,所以自我感觉和地主康锡雪一类人。而电视剧中的二先生则没有和康锡雪的阶级认同及心理亲近,所以其言行更接近众村民和民兵。最大的区别是在除夕夜日寇进村屠杀这一情节中,小说中的二先生看到日寇惨杀村民逼问民兵下落时,吓得想要屈服。而在电视剧中,同样的情节,二先生则是面对日寇威胁顽强不屈,最后和日寇拼命而被杀害。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开明绅士高参议属于统一战线中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政府高官有交情,同时又为中共做些内线工作,但在小说中戏份很少,从主人公杨晓冬的视角来看,虽然需要利用高参议,但却不时地轻视后者的工作成效甚至工作方法。后来,当高参议谈了他对争取伪省长的工作思路时,“杨晓冬看出高参议既真爽又矜持,满带学者的派头,把复杂的政治斗争看得过于简单”[68],所以他对后者是一通教育“因为跟我们谈话的是敌人,跟敌人打交道,要提高警惕,不能简单化,不能先考虑个人荣辱得失。我跟高老先生是初次见面,有个感觉,觉得老先生把问题看得容易了些,考虑个人面子多一点。”[69]从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参议仍是属于被教育和改造的士绅一类,属于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到了2005年的同名电视剧中,高参议不仅是游走于国民党、共产党间的中间人物,甚至还和日本人也有师生之情,成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有民族大义和血性,当日本人严刑拷打他甚至以死威胁他时,他都凛然不惧、不断斥骂。在他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大骂汉奸并且赋诗的时候,镜头采用的是仰视角,通过悲壮的场面渲染了人物英雄气质。
从剧中高参议的言行来看,他显然是不需要被批评和改造的,其不畏拷打和从容赴死的壮行,以及最后去往革命根据地的结局,都接近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主要正面人物形象了。
新时期影视剧对乡绅阶层的宽容、理解或重塑,一方面体现了时代语境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是对某些过去被遮蔽的历史事实的重新去蔽。在相关史料记载中,是存在家业丰厚的地主为抗日不惜毁家纾难的事例的。但这些个别事例在红色经典“抗战”小说中被忽视了。另一方面,上述影视剧把所有本属于中间势力的人物塑造成了有民族大义和政治觉悟、最终壮烈牺牲的进步力量,又是矫枉过正,没有反映出抗战时期阶层分化和抗战工作及人性的复杂性,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假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