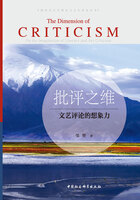
第5章 他者镜像: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与中国文论的主体性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的《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对美国比较文学的“垂死”之由展开深入分析,并且试图以一种极其理想化的方式重建比较文学“新生”之路。国内有学者对该书的理论框架和主要思想进行过批判性解读,但没有能够以“他者”为镜、站在主体性立场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事实上,“他者”的艰难境遇并不意味着“自我”发展的契机,尽管各自的主体性不一样,但从“他者”的反思能力中观照“自我”思考的参照系,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36]。从这一意义上讲,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为思考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的主体性问题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思考向度。
一
《学科之死》对美国比较文学的衰败颓废之势直言不讳,并总结出造成这一现状的两大主要缘由:其一为比较文学在“跨越边界”过程中的“有限渗透性”问题,斯皮瓦克认识到由于欧美长期操持语言文字领域的话语霸权,边缘国处于被放逐的失语状态,比较文学实际上是欧美文学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强势输出和单向度传播。权力关系的极度不平等使得比较文学在由边缘国“越界”到宗主国时遭遇重重困难。斯皮瓦克分析道:“比较文学必须跨越边界,德里达从未停止通过引述康德来告诫我们,跨越边界是问题重重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从宗主国出发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边界,然而从所谓的边缘国出发却要遭遇官僚政治和警察管制而设的边境。两者合在一起则更难跨越。虽然全球化的影响已经遍及世界,尼泊尔的村庄里也安装了卫星电视天线。但是,与之相反却永远不能实现的是,日常生活细节、生活状况以及沉积许久的文化习俗等的影响,却未能在拥有卫星的国家出现。”[37]针对宗主国为所欲为地对边缘国进行“命名”和“绘图”,斯皮瓦克—针见血地指出:“对于新的非洲世界来说,旧有的未经划界的非洲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而对比较文学而言,它根本就不存在。”[38]造成比较文学危机的另一症结,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对人的“不可判定性的恐惧”。斯皮瓦克分析了资本与英语的世界霸权地位造就了比较文学与生俱来的欧美主导性,同时也是导致比较文学衰落的重要原因。欧美主流文化主导下的比较文学跨界进入边缘国时,他们试图站在主体位置去了解和追寻他者的意义,但最终却无法从异质性主体身上找寻到有关他者的信息。“他者”已经是经过过滤之后的自我理解场域中的“他者”。
斯皮瓦克对比较文学濒临死亡的症结分析,为我们思考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主体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他者是谁?”“他者在我们的眼中如何?”“我们与他者之间的对话有无可能?”诸如此类的追问隐含着十分重要的问题意识:中国文论要在当今纷纭复杂、差异丛生的学术话语场域中夯实自己的地位,仅仅依靠“中西文论对话”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宏大命题的提出,或者简单化的资源整合,都是远远不够并且违背初衷的。中国文论面临着“理论的漂泊”和“理论的异化”双重创伤,交织着奥德修斯(归依故土)和忒勒玛科斯(寻父)的双重焦虑。“主体性”是当前中国文论建构的必由之路,一如斯皮瓦克的焦虑,遭遇“理论漂泊”的中国文论在西方文论的强势话语包围中陷入背离本土情境,以及在文论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自我他者化的尴尬处境。近年来,中国文论界充斥着“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中华性与现代性对举”等等论调。毋庸置疑,学者们对20世纪以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批评、解释学与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急剧输入并迅速占据学术话语的核心圈层表示忧虑。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建构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与西方文论的博弈与对话中,确立“何为主体”“何为参照系”的问题。
中国文论在与西方文论的博弈与对话中,存在着两种误读“主体”与“参照系”之间关系的表现:
其一,中国文论在西方文论的话语狂欢与理论的能指游戏中丧失对自我主体性的坚持固守,陷入甚至彻底迷失在对西方文论的顶礼膜拜中。温儒敏教授在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重点论述了十位中国批评家的理论及其实际批评,这十人无一不是“拿来”西方的文学理论,该书列举了王国维对亚里斯多德关于悲剧功用的“卡塔西斯”说的“拿来”、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以及对康德“美在形式”的挪用,在评价朱光潜对西方文论和美学的接受时认为,“朱光潜的直接的理论源头包括康德、叔本华、尼采,一直到克罗齐的所谓形式派美学”[39]。他“几乎是抱着难于抑制的兴奋从这位意大利人(克罗齐)这里搬运了很多东西”[40]。中国文论的研究者,常常对于西方文论“俯拾即是”“拿来就用”,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三号《译书感言》里提出,“中国的学问和西洋人相比,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离,但是,我们只需要几十年的光阴就可在同一个文化的海里洗浴了”,所需的方法是“他们发明,我们摹仿”,他们“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们“俯拾即是”[41]。茅盾也曾就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接受发表意见,“中国一向没有正式的什么文学批评论。有的几部大书如《诗品》、《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文学批评论,只是诗、赋、词、赞等等文体的主观定义罢了。所以我们现在讲文学批评,无非是把西洋人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42]。当代西方文论的介入无疑为众多学者提供了炫弄理论时髦话语和故作高深提供了机会,种种谬误不通的“X比Y”式的比较诗学论文充斥着各级学术期刊,冠以“post”前缀的后学专家们言必称父权、流亡、后殖民、族群、女性主义等西方文论术语。面对这种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的西学之风,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樑先生深有体会,他引述过一位中年教授的自述,“我以前搞过心理分析研究,现在它已过时,我已转而投入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了”[43]。综而论之,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从广义的西方理论,再到苏联模式的马列文论,基本上处于一种自我放弃主体位置、在将自我他者化中沉迷于理论的话语游戏,从而在全球化的理论场域中长久地飘在异域,游离于边缘的边缘之外。
其二,借“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之名,希冀通过单方面的文论输出来证实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力和有效性,具体做法是以中国传统文论的某些关键概念为“元理论”去阐释西方文学,进而建构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体系中的全新格局。必须承认,中国古代文论(主要体现为文化思想)的确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发展长河中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世界,艾兹拉·庞德的意象派理论就深受中国古代文论“意象说”的影响,尤金·奥尼尔的戏剧理论也受惠于老子的文论思想,但如果鉴于此就试图以“中国传统文论”为主体,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在一个静态的观照中推介中国传统文论在全球化中的渗透和影响,就显得极不现实。国内有学者尝试过以中国古代文论去阐释英国文学,文章兴致勃勃地采用“言不尽意”“神用象通”“立象尽意”“以少总多”等中国文论关键术语去分析康拉德和吉卜林的小说,作者很肯定地判断,“1894年和1895年先后出版的两部《丛林之书》,显示了吉卜林在表达印度主题时使用的‘立象尽意’或‘神用象通’法”[44]。作者在文章的结尾总结道:“吉卜林、福斯特等英国作家似乎深刻地领悟了‘立象尽意’和‘以少总多’的中国传统文论精髓,并在其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实践之,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使他们的文本成为英语文学中的力作。这同时也说明,中国文论的某些基本原理表达了人类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因此,它对于东西方文学具有分析阐释的普遍价值。”[45]以此类推,似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乃至《文心雕龙》的所有文论术语都能从西方文学中找出可供分析的对象。这种将对方绝对“去主体化”、以静态观点力求找出中国文论在西方文学中的价值显现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向度上都缺乏合理性。只要稍微回眸中国文论在海外的接受现状,就能管窥出抽离语境生硬外销中国文论其实只是一种自恋行为,或者是国内文论界自我满足的一剂迷药。20世纪西方重要的文论家T.S.艾略特、诺斯若普·弗莱、特里·伊格尔顿、韦恩·布斯等的著作中,绝不见中国古今文论的只言片字,的确处于一种完全的“失语”状态;西方重要的文学批评词典《批评理论辞典》(A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1)一书中,收录有中国文论的词条,但都是20世纪50—60年代那些与当时政治相关联的词语,如“庸俗社会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索引部分还把日文的kyojitsu误作中文词汇[46]。《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引》只有Chinese theory and criticism(中国理论与批评)一个条目,这本指引里的L字母里有Lacan,F.R.Leavis,G.E.Lessing,Longinus,Lyotard,甚至有小说家D.H.Lawrence,就是没有Liu Xie(刘勰),Lu Ji(陆机),当然更没有James J.Y.Liu(刘若愚)[47]。即使以《镜与灯》蜚声中国学界的德高望重的艾布拉姆斯,他在其名作《文学术语辞典》中也对中国文论完全视而不见。由此可见,中西文论双方在历经自我内部建构、互看、对峙之后,进入了博弈与对话阶段,“以西释中”和“以中释西”都是将自我与他者限定于一个静态的交流场域中,前者忽视了对自我主体性的捍卫,后者则是对他者主体性的漠视,因而都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48]。
二
斯皮瓦克在精辟分析比较文学的“垂死”之由后,精心地勾勒了比较文学的“新生”之路。首先,她认为应该将比较文学这一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中的区域研究联起手来,“没有人文学科的支撑。区域研究仍将只能以跨界的名义越过边界,但是如果没有改造过的区域研究的支持,比较文学仍将被禁锢在界线之内而无法跨越”[49]。斯皮瓦克反复重申其引入区域研究的真正意图,“我并不赞成学科的政治化,我一直在竭力倡导对敌意政治的去政治化,并且欢呼一种友好政治的来临”[50]。究其实,斯皮瓦克希望利用区域研究的资源,准确地说是区域研究的两个特性:田野作业和注重对边缘地语言的精准掌握,同时避开其“政治性”所带来的敌意,从而促成超越欧美中心主义,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研究和以语言(例如中文、日语、韩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东南亚各民族以及非洲各民族语言等等)为轴心的区域研究相结合。其次,斯皮瓦克认为比较文学必须克服“他异性”,期望以一种极为理想化的“星球性”(planetarity)来取代“全球化”。事实上,“星球性”是斯皮瓦克构建的试图实现“友好政治”并且远离西方中心主义的乌托邦,可能她自身也领悟了这一乌托邦的空间终究无法实现,所以《学科之死》未能对这一比较文学“新生之路”做更多令人信服的阐释。
斯皮瓦克构建的两条“新生之路”尽管充满着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彩,但是以其为镜,恰恰折射出中国文论主体性构建和固守的两个重要策略。其一,中国文论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其理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价值体系的现代转型、理论资源的现实效用均可借鉴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方法。可以说,以当代性、边缘性、实践性和跨学科性为基本特征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蓬勃兴起、文学性蔓延的现实语境中,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诸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以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文本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范式。赞成也好、反对也罢,文化研究的确在文艺理论领域安身立命并以极其迅速的态势攻城略地。一方面,借用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中国古代文论中长期被忽略的边缘话语(比如通俗小说、民间戏曲)重新被发现被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在进行所谓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研究重视历史、语境与意识形态的学科品格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另一方面,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尚未进行有效的本土转化,如果将外来进口的文化理论不加分析地套用于中国文论,那将对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带来极大的挑战。当前有学者提出所谓中国文论“理论的异化”,其实质就是担忧在经历“文化转向”之后,人人似乎都意识到了“黑格尔的幽灵”,高谈阔论“文学终结论”,研究文学的学者也纷纷改弦更张,开始研究媒体、族裔、赛博空间、酷儿理论。笔者以为,文论的研究对象虽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学文本,但是当文论的研究对象蔓延得无边无际、文学的身影被挤压到绝对边缘时,文论也将彻底被“异化”,更何谈主体性?艾布拉姆斯曾用“回音室”的著名比喻来批判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里达的文本之室是一个封闭的回音室,其中诸多意义被降格为某种无休止的言语模仿,变成某种由符号到符号的横七竖八的反弹回响,它们如不在场的幽灵,不是由某种声音发出,不具有任何意向,不指向任何事物,只是真空中的一团混响”[51]。如果说没有意义的文本只是玄虚的幽灵般的能指游戏;那么,不以文学文本为研究中心的文论也就无法奢望主体性。由此可见,引入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有助于中国文论的自身建设,但同时必须警惕“理论的异化”,始终坚持以文学文本为中心。
其二,斯皮瓦克关于理想化的“星球化”的描述,其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强调中心与边缘互为主体,以及建立所谓“友好政治”的诉求,为当前中国文论“理论的漂泊”提供了重新定位“主体位置”的启发。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的平等对话能否实现,最根本的前提是要置双方为“主体”——互为异质性的主体,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反对狂躁而充满空想色彩的中国文论世界化的论调。一方面,“中国传统诗学迫切需要更新重建自己的现代话语系统,但是为着重建自己的话语,它又没法不借助于参照系,也就是说,不能不以大军压境的西方话语作为参照系”[52]。因而,承认人类审美心理的基本共通性、文艺的历史类同性、诗学话语的历史性以及电子传媒时代的信息共享性,同时放弃僵化的文化意识形态与文化本位主义,在充分认识到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文论的对话,这是固守中国文论主体性的根本所在,钱锺书关于“通感”的讨论、张隆溪从阐释学论述“道”与“逻各斯”、叶维廉的中国诗学都是卓有成效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国文论在承认自我“时间性”的差异后,应该敢于超越传统意义上关于阐释者与被阐释者之间主客对立二分的局限,利用对方的文化资源,抓住机会主动提问,“是处于主动发问的位置,还是处于被动回答的位置,其对话的效果也会明显不一样。谁取得提问的权利,作为话题的‘问题’或者说‘主题’就在问题意识和追问的方向上较多地倾向于提问的一方”[53]。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这样评价《学科之死》,“斯皮瓦克的观点很具个性,也很激进;从她的贱民观和对贱民的研究来看也是很合理的。这种理论源于她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由该历史所决定的视角。”[54]以他者为镜,斯皮瓦克的激进的、不乏理想化的对比较文学“垂死”之由和“新生”之路的理论阐述,为思考中国文论的主体性提供了有益参照。比较文学不会“死亡”,比较诗学仍将继续发展,只要坚持有效的主体位置,把握时机主动发问,中国文论就能从“理论的漂泊”和“理论的异化”的双重困境中突围,并且在与西方文论的动态交流场域中固守其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