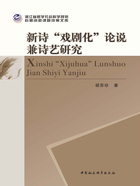
序
吴晓
本书是胡苏珍在其浙江大学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完成的。百年的中国新诗史,是创作上不断探索、理论上不断丰富的历史。其间产生多种流派与思潮,演绎多种主义与主张,从而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新诗创作及诗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其中一些时显时伏的诗学主张或命题,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影响。“新诗戏剧化”论说就是这样一个贯穿几代新诗而概念至今不明的话题,是一个需要系统梳理、阐释的新颖学术课题。胡苏珍多年在高校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有着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审美直觉,对诗歌认真致敬。因此,当她选择以新诗戏剧化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时,我作为导师是非常支持的。
史上各种“新诗戏剧化”创作及理论,有其诗学的合理性及古今中外的理论渊源。在新月诗派,有不少诗人做过创作方面的实践探索,涉及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等。然而作为诗学主张集中加以倡导,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事,诗人兼诗论家袁可嘉更是提出“新诗戏剧化”方向。他针对当时诗坛存在的说教与感伤两个通病,结合英美新批评诗学理论和40年代西南联大诗人实际创作,倡导“生活经验”与“诗经验”须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这种“戏剧的表现”最大的特点就是“客观性与间接性”;并结合现代人经验、情感的复杂矛盾特质,提出一首诗要融合各种“相反相成”的戏剧性思想和情绪。这就是他的立论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知名诗人都谈到自己诗歌创作的“戏剧化”追求,又不同于袁可嘉的说法。总之,新诗戏剧化论说的出现和实践,涉及的不仅仅是诗歌艺术表现的问题,更在于对丰富现代诗精神的理解。当然,袁可嘉把它作为实现“新诗现代化”总体目标的一种途径来看待,其中有无本质化嫌疑值得讨论。
古人说,“诗缘情”。诗作为情感的艺术,是用来抒发情感的,但诗却不宜直接表露情感,也不只是表达感情。中国古人也有一句话,叫作“一切景语皆情语”。这里的“景语”其实就是“情语”的“形式化”,是情感的“客观对应物语”。因此这句话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一切情语须景语,”也即“情语”必须通过“景”来表达。在我看来,新诗戏剧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与上述说法是相通的,但又不能看作雷同。袁可嘉反对的诗界弊病,说教、赤裸的陈述、宣泄无余的呐喊等等,确是“非诗的质素”,离诗甚远,袁可嘉提出“客观化”“复杂化矛盾经验”,符合诗歌本质规定和现代语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戏剧化”写作包含了诗人对以往个人抒情的调整,把情感变为“意识”和“经验”,从自我扩大到他人,容纳情境、场景、细节、对话、冲突等等,深入时代和语境,并兼顾诗美境界,无疑应该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正是从上述史实和诗学基本原理出发,胡苏珍对新诗戏剧化论说及写作,从源头到演变、从美学形态到理论思路等各个层面展开了整体梳理和全面阐释。
更可喜的是,胡苏珍透过某些现象,进一步探索戏剧化理论的实质及其内在的价值。作者根据近百年新诗实践,把新诗戏剧化方式分解为下述三个层面:一是言说主体的戏剧化,二是诗思的戏剧性,三是表现手法的戏剧化。作者以此建构了一个相对较完整的体系,有益于我们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
面对“新诗戏剧化”说,也许会出现质疑的声音,这其中涉及“戏剧化”这个概念的问题。不过,不论是“戏剧化”,还是“化戏剧”,大可不必计较“戏剧”这个名称。在我看来,倡导者未必一定是要诗家向戏剧家看齐、要前者向后者取经。倡导者只不过是借“戏剧”这个名称来表述某种意思,概括诗歌的某种表达方式、路径而已。
因此胡苏珍在文中强调:
现代汉语诗人的“戏剧化”写作并非导向“戏剧”的激烈事件冲突或在一个一定长度的动作过程中展现人物的命运,而是仍留在了“诗”的园地,存有诗的抒情性、主体性、想象性及语言的非陈述性等内在的文类特征。从戏剧化写作三种内涵形态来看,包含诗人由“自我”向“角色”生命意识拓展,由单线情思向“矛盾复杂经验”的包容,由戏剧化“场景”推进诗思和创新语言的生成,因此,戏剧的角色、矛盾、场景等美学理念与要素只是帮助诗歌拓展文类表现范围和表现深度的策略或途径。
这可以说是作者对于戏剧化理论的实质的揭示,也是作者的基本态度和评断,当是十分准确。显然,诗中的“冲突”“对话”不等同于戏剧中的“冲突”“对话”,二者虽是同一概念,却不会是同一种状态或程度。所以,本书探究“新诗戏剧化”,并不是停留在外围讲“文类融合”,而是探讨几类戏剧化形态对“诗”的丰富,建立在对诗歌本质的思考基础上,并结合了大量的文本细读。总之,本书的思维亮点很多,有待深化的问题自然也存在。
我向来认为,对任何一个学术话题,研究者不仅需要准确精细地还原它产生的历史、发展的历程,准确描述其基本形态、表现特征等,更应该探究其内在机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对其作出本质的把握。看待一个诗学命题,不在于其“说了什么”,也不在于前人为什么说,意图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把所有的历史陈述,重新加以激活,以你当代人的眼光,以你独特的观点去加以解释,加以重组,建构你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不是历史牵着你走,是你引领着“历史”走;不是材料主宰你,是你主宰所有的材料。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是历史重要,还是你的认知重要?是该相信历史,还是该相信你?尊重历史“真实”固然重要,那是前提;揭示历史资料的本真,才是更为要紧的。这篇博士论文,作者做到这个程度,的确也体现了这一主张。胡苏珍聪慧专注,思维敏捷,感悟力强,本书的完成显示了作者的理论素养和学术研究特点,在纵深探索中实现了自我建构。
是为序。
2018年12月 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