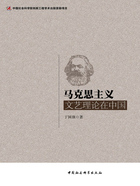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译介与探讨
一 对马恩文论经典的译介与研究
如前文所述,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的一些文艺理论论著就已经被介绍了进来,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方面的译介有了更大的发展。1953年2月国家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除此之外,一些学者也通过有选择性地译介马恩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著作,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译介方面,主要是王道亁等人的翻译。如王道亁翻译了《恩格斯论海涅》一文,该文选译辑录了几段恩格斯论海涅的文字,所选文字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对海涅的赞赏,也有对海涅过失与错误的批判。[1]王道亁还辑译了《恩格斯论歌德》一文,主要是恩格斯论歌德的三段文字,主要有《卡尔·葛鲁恩的论人类观点的歌德》(今译《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1847年1月15日致马克思书》等。[2]这在当时马恩全集尚未出版的情况下,对于人们了解恩格斯的文学观及其如何看待歌德的价值与观念很有意义。“我们并不以道德观点或党派的观点责难歌德,而至多以美学及历史观点责难他;我们衡量歌德既不以道德尺度,也不以政治尺度,更不以‘人的’尺度。”这段译文的发表,较早介绍了恩格斯评价文学作品的“美学”“历史”的评价标准。另外,王道亁译的《恩格斯论卡莱尔》[3]在《文汇报》上分两次发表,集中译介了恩格斯在《英国劳动阶级状况》《英国现势卡莱尔的〈现在与过去〉》《汤玛士·卡莱尔:末日与杂文》等文中关于评价卡莱尔的文字,批判了英国历史学家T.卡莱尔的唯心史观,初步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1954年第1号《电影艺术译丛》发表了邵牧君译自1953年6月23日《新德意志报》、由W.贝逊勃鲁赫所写的《马克思论戏剧中的冲突》一文,文章从“对剧本‘西金根’的批判给予我们的启示”“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问题”“蒙泽尔——乐观主义悲剧的英雄”“党性和客观真理”“个别现象和普遍现象”“反对无冲突论”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比较全面地梳理了马恩列斯等有关戏剧冲突方面的文艺思想。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由法国学者弗莱维勒(J.Freville)编辑、王道乾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书。以上这些文章的译介为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提供了资料保证。
其次,理论研究方面。“文化大革命”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大家所熟知的几封通信展开,涉及的问题包含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几个方面,关于艺术的真实性、文学的倾向性、文艺作品的评价与批评等问题,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很好的研究。例如,程代熙在《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读书札记》一文中论述了历史剧的“真”与艺术作品的“真”的问题,并提出历史剧要做到历史生活的真实,真实地再现历史生活的看法。该文认为,历史剧在创作中可以有想象与虚构,但想象和虚构也必须与历史生活相吻合。[4]马家骏在《恩格斯论历史题材的戏剧——纪念恩格斯诞生一百四十一周年》一文中则通过对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的分析探讨,指出了历史剧写作的基本原则问题:“美学的观点和历史观点”、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以及“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5]关于文学倾向性问题,樊篱在《读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一文中分析了恩格斯所提出来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性问题,认为“应从文学的特点和工人阶级的战斗需要出发来解决文学的倾向性问题”[6]。解驭珍在《关于文学的倾向性——重读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几封通信》一文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文学都是有倾向性的,“一切否定文学的倾向性的论调,都可能导致文学回避当代的重大政治斗争,耽溺于主观主义的空想或自然主义的琐屑的描写。其结果不只丧失无产阶级艺术的战斗作用,实质上就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损害无产阶级革命利益”[7]。朱建良在《恩格斯论文学的倾向性和真实性——读书札记》一文中则具体论述了倾向性与真实性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在恩格斯那里,文学的倾向性和文学的真实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而又是不可分割的概念,二者是辩证的统一。恩格斯既重视文学的倾向性也重视文学的真实性,因此,不能断章取义地理解恩格斯在不同地点或时间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些论述,而必须将他关于文学的倾向性与文学的真实性的关系这些全部观点统一起来理解。[8]
再次,关于文艺批评的问题,夏康达《重读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所想到的》一文针对某些文艺批评中所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即“在从作品实际出发的口号下,迁就作品,有意无意地放弃了文艺批评的客观标准和时代要求”,提出了批评意见。作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文艺批评实际上成了文艺欣赏,只能欣赏不能批评;这样,文艺批评也就成了作品的尾巴,哪里还谈得上指导创作”。作者指出:“文艺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从作品实际出发,但这并不妨碍、也不应该妨碍贯彻文艺批评的客观标准和时代要求。”[9]郝孚逸《拉萨尔的〈弗朗莰·封·西金根〉和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批判——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信的笔记》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一个领域,也是在斗争中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为此,只有联系特定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条件,比较全面地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拉萨尔之间争论的有关材料加以研究分析,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信中指出来的主要分歧点,才能够确切地理解其中所阐述的若干美学原则的基本观点和深刻含义。[10]另外,杜铁柱从恩格斯对待拉萨尔的剧本《西金根》的态度上受到启发,分析了从事文艺批评的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养。作者认为,“这种认真准确、热情具体的批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11]。文章还批评了当时文坛所出现的一手握框框,一手操棍子,以及某些在批评上盲目吹捧的不良苗头。
相关内容的探讨还有很多,而且在分析上也越来越深入。刘纲纪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一文中着重介绍了马恩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德国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并不表现在他们作为一个政党所进行的实际的政治斗争,而在于作为一个著作界、文学界的流派所进行的关于“人性”“爱”“良心”“人道主义”等的“美文学式”的宣传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即是人道主义,而马恩则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清扫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人性论”的理论流毒。“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1)向“富人”们进行人道主义说教;(2)同时尽力描绘“穷人”的苦难,以引起“富人”的同情;(3)制造种种关于幸福乐园的廉价幻想,以慰藉终日陷入苦难之中的“穷人”;(4)“‘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大的忧郁病患者”。马恩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学发生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在批判中,马恩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学最本质的特征以及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战斗的文艺批评的典范之作。[12]
由于研究的深入,当时还出现了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引起了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如蒋培坤在《读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一封信》一文中针对赖应棠的《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13]一文的表面化理解提出了看法。作者认为,“恩格斯在那段话中[14]所阐明的,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特征,还包含有更重要的一个内容,即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所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文学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的辩证统一;与此同时,批判了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创作倾向”。作者结合时代和信的具体内容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当作家描写他所深刻理解的生活时,他的主观倾向才能得到真实有力的表现,因为这种倾向性,亦即对人物事件的一定政治态度和感情倾向是深深地扎根于对生活的真实体验的”[15]。《学术月刊》1965年4月号上,勇征之发表了《不许假恩格斯之名来反对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一文,文章认为,《城市姑娘》通过一个“陈旧又陈旧的故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阶级矛盾,暴露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所以恩格斯才称这部作品是“除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敢”。对此种看法,昭文、凌柯写了文章予以商榷,认为勇征之同志对于《城市姑娘》这部作品本身的评价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所做出的判断是错误的,虽然恩格斯在信的开头谈了《城市姑娘》的优点,但“这封信的重点是在于对这本书所作的批评”,恩格斯指出了哈克奈斯的一个最根本的毛病:她只写出了“细节的真实”,而没有“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16]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这些争论,对于当时人们更好地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除以上内容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文艺著作也继续被中国学者引介到国内,主要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当代美学家里夫希茨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1958年)和《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册)(1960年)。正是借助于这些译本,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那些没有译介过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的文艺思想,也开始由中国学者借助于外文(主要是俄文)资料展开了初步的研究。
当时涉及的理论问题主要有: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戏剧冲突、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民间文艺、作家评论等。如王亚南发表的《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上)——马列主义的文艺观》(《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陈瘦竹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介绍》(《上海戏剧》1962年第6—11期),周来祥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山东大学学报》1960年第Z1期),胡经之发表的《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6期),郝孚逸、刘崇义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人道主义》(《学术月刊》1964年第9期),刘纲纪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美学的根本对立——评工农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看法》(《美术》1964年第5期),北师大中文系列宁著作学习小组发表的《捍卫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光辉战斗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等都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张怀瑾发表的《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过时了吗?》[17]一文,文中针对周来祥在《文艺报》1959年第2期发表的《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一文所提出的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过时论”作了回应,认为周文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已被艺术生产适应于物质生产的新现象所代替”是值得商榷或重新加以探讨的。作者认为,首先,周文所理解的,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两个基本含义,即“在艺术领域内各个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整个艺术领域和社会的一般发展的不适应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把两者并列起来就显得重点模糊,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相一致了。其次,周文对马克思的“把希腊人或者甚至把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这句话,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又机械地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即没有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类型和阶级社会的类型。最后,更主要的,周文还有另一个不正确的主要论点,这就是“在我们的时代,马克思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学说已经过时了”,“旧的条件消失了,马克思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也过时了”。文章认为,这只能说是“发展”了而不是“过时”了。李基凯、梁一儒也发表文章《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问题》[18]对周文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这是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较早讨论。
从延安以来就有着极好的重视民歌传统的中国文艺界,在这一阶段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和恩格斯的《德国的民间故事书》(《民间文学》1961年1月号),这些集子和文章的译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评论。另外,1960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艺术问题的几封通信[19]开展了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从而厘清了一些过去有些分辨不清的问题,如“现实主义”理论、关于文学倾向性与真实性的关系等。这一阶段发表的文章基本属于学习札记形式,学者们边学习边体会边研究。1949年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年,也是斯大林的70岁寿诞之年,加上几年之后,即1953年,斯大林去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中,斯大林的文艺思想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很好的介绍与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总体上来说,“文化大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探讨,在我国还是以介绍为主,学习为主,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仍较为肤浅,难以深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著也多以单篇形式被一些有见识的学者翻译出来或成书出版,而大部分的学术研究则基本还是用俄文版的“马恩”论著。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尚未出版或只有部分出版,并没有流行开来。[20]关于马恩等经典文艺理论家的文艺思想探讨,在新时期以来得到了更多更深入的研究,相关的研究资料也更加丰富,并日益同我国的文艺创作实践结合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性论文不多,有限的文章也大都与政治话语比较接近,或以政治的视角用马列的基本思想来解读与政治本来相距较远的作品。如任范松的《坚持文艺党性原则破除“艺术私有”观念——纪念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七十周年》(《延边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杜小军、刘亭的《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读列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求是学刊》1975年第2期),杨国援、陈梦炯、兰克、黄思银《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学习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思想战线》1975年第4期)等是探讨文学党性问题的。1975年第9期的《河北文艺》发表了一篇文章《为无产阶级专政立功——读马克思在一八三六年写的一首诗札记》,这篇文章以195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马克思在1836年创作的一首诗[21]为解读对象,认为这首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号令与武器。“文化大革命”之后,《杭州文艺》1978年7月号重新发表了由薛菲翻译的这首诗[22],在译述中译者介绍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并认为从诗中读到的是一种激情的力量——“只有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理想和全人类的未来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产生的那种高贵的激情的力量”。对同一首诗,所做出的解读上的差别,让我们看到了时代所打上的明显印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是如此丰富多彩,而几乎所有内容又都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在有限的篇幅内要想有个全面又详尽的了解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本书只能选择几项内容予以论述。关于前30年该理论的研究进展,本书将重点介绍马恩经典作家关于民歌、民间文艺的看法,粗略梳理学界对马恩文艺思想中一些经典理论的初步研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斯大林文艺思想的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