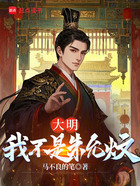
第41章 挖煤(求追读)
第二日,结束禁闭回到东宫,
方孝孺莫名感觉不习惯,
朱允炆罕见地没有抓住他一股脑地问一些自己根本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而是让方孝孺做最喜欢的事情:读史,
这个中年儒士不由得兴致高昂,提高了自己的音调朗诵,大声背诵近日正在阅读的《春秋本末》:
“先中国而后夷狄,义例甚精,皆圣制也.......”
朱允炆瞪大眼睛盯着摇头晃脑的方孝孺,
目光却有些失衡,
目光的失衡源于心态的失衡,
这种失衡并非源自于“因为权力的过度集中,错误的选择导致了错误的结果”,
更不是源于朱元璋对此事真相表现出来的毫不在乎,反而对他大为嘉奖的事实,
甚至不是源于他觉得自己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错。
事实上,他自己也并不特别在意这群人到底是不是符合他想象的邪教,
而是他失落于在玉佛儿死掉的那一刻,才恍然明白,
洪武帝赋予的“指挥使”这份权力,被他用在了内部消耗,对付流民百姓这种事情上......
他本来可以用来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
“有些东西,是注定无法逃避的,只要我被摁在北镇抚司锦衣卫指挥使的位子上,我就必须参与其中。”
朱允炆摸着自己的心脏,直面自己在面对危险政治问题时的软弱,
“蓝玉的死,可以视作是一个转折点,极致的压力下,那根武将与皇室之间的默契之弦被崩断了,对于任何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实事来说,一个公认的大事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此时此刻,就有很多文臣武将被锦衣卫监视,受到隐形的迫害,但我却把精力放在了对付白莲教身上。”
朱允炆在心里默默想着,方孝孺的话语就像是耳旁风一般刮过,
“任何一个人,对洪武帝的恐惧都会在他们心里被放在第一位,即便是我父亲,都更加畏惧于皇爷爷的威迫,反而是为了我,能在朱元璋面前说出【我儿畏德不惧威】这种话来。
但我不能被这种恐惧支配,强大的权力伴随着的是艰巨的责任,若只想享受权力带来的满足与愉悦而逃避权力带来的责任和那些自认聪明的亡国之君又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我的务虚能力和务实能力并不匹配,陷入了【当局者迷】的陷阱里,代入猜忌,怀疑,不信任的视角中,遥站在上帝视角,忘记了对事物客观认知的基本条件就是调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朱允炆将自己穿越之后做过的事情全部复盘了一遍,懊恼与悔恨之意充斥在心里,
“我但凡产生一个偏颇的认知,对一个甚至几十个,几百个普通的百姓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密密麻麻的汗水顺着脊背流下,
朱允炆终于明白掌握了超出常人能获取的信息带来的反噬后果,
他即便高度认同自己皇室嫡亲的身份,也无法完全地摆脱一个现代人的思维去思考事情,
“蓝玉案还未成定论,还有更改的机会。
蒋瓛也许早就被洪武皇授意,也许是因为我父亲的去世导致了朱元璋的滥杀,更有可能是蓝玉本身就有问题,这里面有太多谜团。
我不能一直以暧昧的态度与蒋瓛相处。
如今我已是都指挥使,于职权之内,我有权过问北镇抚司的内部事件;于私心,我也可以和博洽结交,培植自己的宗教势力。
家国天下,我如今并非皇太孙,不必处处为自己设限!”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朱允炆抬头,摆脱了负面情绪的影响,从心流之中退了出来,顿时觉得方孝孺的高声朗诵有些聒噪:
“方孝孺,停下!”
方孝孺打了个颤:“圣孙,您不想听了吗?”
“陪我出去一趟,这几日姚广孝是否与你有书信往来?”
“有的,有的,圣孙,我都背下来了,信件我都保存着。”
方孝孺连忙把随身的书信拿了出来,
虽然同一个和尚通书信不是什么“错误”,
但他的政治敏感度在跟着朱允炆耳濡目染的熏陶之后有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联想到其中的政治意义,他还是会感觉到紧张和担心,
朱允炆吩咐道:“陪我去大天理寺找博洽,路上你把书信内容背给我听。”
“是。”
“另,林大在诏狱提来复,叫薛定善再审一次,我下午回北镇抚司衙门......”
“结案。”
他把“结案”二字说得很重,白莲教教众今日审讯会出结果,
除了匪首“玉佛儿”在子时左右便死掉了之外,其余人还在审讯之中,
“是。”
林大毫无凝滞,转身离开。
朱允炆拉着方孝孺出东宫,备车往大天理寺去的时候,
燕王朱棣正在姚广孝的陪同下参观西山煤矿的改建工程模型,
毕竟改建煤矿不是一时之事,
而西山又是一处水源极其丰富的矿产,只要开窑挖煤十有八九会漏水,
贸然改造或强行上马工程,会造成人员的伤亡不说,也会极大妨害工程的进度,
毕竟如果改造得当的话,成倍地增长煤产量不是问题,
因此经过北平铁冶所人员对《开物书》的研究和审视,采用了一些书中记载的方法,竟然发现里面蕴藏的煤矿竟然接近于“取之不尽”,
那么最先要解决的,就是“渗水”问题了。
“燕王殿下,这等小巧的机心着实善用,只需多立几根【承力柱】便使得内里稳固了许多,只是如果要在矿里实用,需要经过验证。”
铁冶所的官员对燕王讲解道,
“比如这个排水的管道,若是通过这《开物书》里提到的螺丝连接,或者‘一体成型’弯接管道,也需要在冶铁过程中改进技术,如今的铁管不是太软就是太硬,并不合用。
但这番改进是由煤矿开始,如同书中所写,必须精炼煤矿,使之达到更高的温度,才能精炼‘钢铁’。”
燕王对此并非一窍不通,但他在意的只有结果:“煤矿的改造,最快多久能上马?”
“最迟月中十五六日就能上马,若是短时期内合用,我们会在北平省内广泛推广。
各个部门都对《开物书》的技术十分感兴趣,已手抄数本,发放阅读。
不少官员正在日夜研究其中提到的铜,金,银的勘探开采技术,通讲给咱们所里的匠人。”
“不错,上通下达,莫要藏私。”
朱棣只是默默点头,再也没有了什么动静,
直到离开铁冶所后,也未发一语。
姚广孝呈上来的《开物书》被铁冶所官员肯定,
什么成倍增长,确有实用性,只待实证等词句在脑子里打转,
坐在回府的马车上,朱棣心中反而生出些许奇怪的腻歪感,问姚广孝道:“那方孝孺不是我大侄子的老师吗?为何突然会这些工匠的活了?”
“燕王殿下你有所不知,我近日已与方孝孺通书信,知晓在他身后的确有一个大匠,助他写成此书。”
“你的意思是那个大匠出身工部,却不向工部呈上此书,单单要把这本书给我,由不具名姓.....这到底是何用意?”
“臣不知。”姚广孝也感觉奇怪,“不过若能助长煤矿产量,炼出那更加坚固的甲胄,锐利的兵器,或许我们能更快收复失土。”
“倒也不错。”朱棣掀开轿帘,突然没来由说了一句,“你说这里面,有没有我那个大侄子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