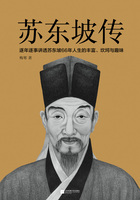
第7章 神宗革新,安石献策
赵宋王朝,自乱世废墟上建立,经唐代安史之乱、黄巢之乱和后来的五代十国之乱,长达六十余年的战争与分裂,政权落到大宋皇朝手里时,已是民困国乏,积弱已深。
开国不到二十年,逐渐强大起来的异族,便开始对大宋虎视眈眈。北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数次南下入侵;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以强悍的游牧骑兵,频频对边境进行扫荡式的洗劫。朝廷不得不在边境设重兵把守,沉重的军费和岁帛又成负担。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兵变取得政权,曾目睹藩镇割据之乱的他,比任何一代帝王都更担心大权旁落,因此,大宋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尤其重视中央集权的朝代。
政权建立之初,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逐渐把军权、政权、财权都最大限度地集中在自己手中。作为宋太祖给子孙后代定下的“祖宗家法”,这种制度代代相传。
对于起自风雨飘摇之乱世的赵氏宋朝,这种制度在建立之初,对稳定政局、发展经济、抵御侵略都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举措的弊端也渐渐显露出来,文臣治国,武备松弛,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臃肿,加之外患不绝,每年要给辽和西夏等大量岁贡,等到宋神宗赵顼继位时,大宋的国库已严重空虚。
苏轼在凤翔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曾指出大宋眼下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财政不丰,二是兵力不足,三是吏治不择。为此,他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应该说,彼时的苏轼,为大宋号的脉是准的,开的药方也是有效的,可惜他的声音太弱,无人听得进。那些如沉疴痼疾一般的积弊,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推波助澜者才能消除。
历史没有把这样的重任交给具有诗人气质的苏轼,而是交给了更富政治智慧与铁血手腕的王安石。
治平四年(1067),在位仅仅四年的宋英宗因病驾崩。同年,赵顼即位,即为宋神宗。神宗为英宗长子,母亲是宣仁太后高氏。
这一年,神宗刚刚二十岁,正是奋力欲为的年纪。还是太子时,神宗就已留心国事,注意到民贫国穷、军政凋敝的现状。富国强兵,也为一报家仇,这样的念头日复一日地冲击着这位年轻帝王的心。
国恨家仇,却为表面的承平盛景所掩。文人治国,士大夫们十之八九皆为文章能手,他们长于纸上谈兵,缺少果断有为的气概,而国家给他们的优厚待遇,越发加重了他们的不思进取。神宗的父亲英宗属保守一派,他不愿意改革,也不愿意与异族发生战争。在他在位的短短四年里,国内国外也相对平静。但那只是表象,平静的水面下早已暗流潜涌。
面对这样的朝局,神宗决定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项伟大的改革,要有领袖与倡导者,也要有有力的支持者与执行者。就这样,王安石被适时地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在打算重用王安石之前,神宗先在朝廷重臣中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得到的答卷让他非常失望。
文彦博是当时为世人所景仰的名臣,神宗对他说:“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
文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但他也仅是附和了一下,并无具体建议。
神宗又与富弼谈论治世之道。
富弼早已清楚神宗的心思,不等他多问,便回道:“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
神宗只得默然。
神宗又去向司马光请教,司马光言道:“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总而言之一句话,要先修身后治国。
神宗看得很清楚,国家眼下最大的困难,在于欲举兵而兵力不足,欲足兵而饷不济。养兵备边、充盈国库、节约财用,这些都是当务之急。但他与这些朝中老臣谈及此事时,他们不是稀里糊涂敷衍了事,就是明言反对。环顾朝堂,满目朝士,竟然找不出一个同声相应者。
这些朝廷重臣也看得很清楚,大宋的积贫积弱,非一场改革所能解决,要沉着冷静、循序渐进地改变此种局面。新皇帝毕竟还太年轻,锐意有余,而持重不足。
一方要求锐意革新,一方力求稳当持重,神宗与这些朝廷重臣难以达成一致。环顾朝廷上上下下,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与焦灼笼罩着年轻的神宗,他太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了。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走进了他的视野。
王安石,字介甫,庆历二年(1042)进士。青年时代,王安石曾随父亲宦游天下,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民间疾苦深有了解,也早早立下经时济世之志。及至进士及第,他又屡辞馆阁之命,先后在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职。在轰轰烈烈的新法推行之前,王安石已经在他任职的地方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尝试,且收效显著,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变法理论与方案。
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那封谏书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任地方官多年的经验,指出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其根源在于不懂得法度,要求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这篇上疏可视为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序曲,只可惜他的改革主张终未被仁宗采纳。
此后,朝廷多次以馆阁之职召王安石入京,均被他拒绝。王安石深知,国家承平日久,朝廷上下都被一种因循守旧之习气所主导,要改革,非得等到时机成熟不可。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数次拒绝了朝廷召他进京的美意。有人说他这是沽名钓誉,亦有人说他在为自己积蓄力量——经验、资历、名望。
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随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越次召对,王安石欣然前往。同抱改革之志,君臣一见如故。就当前国事,神宗向王安石提出许多疑问,王安石侃侃而谈,神色自如。十年磨一剑,经仁宗之后近十年的磨砺,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已更趋完善与成熟。
“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蛰伏太久的王安石终于扬眉吐气。
而笼罩在神宗心头的愁云,也为王安石的那番豪情一挥而散,改革的决心与信心更加坚定了。一个力主改革的年轻君主,一位满腹变法主张又富有实践经验的臣子,一场影响后世的伟大变革,终于在此时奏响了号角。如同一股不可遏制的汹涌洪流,“熙宁变法”(也称“王安石变法”)冲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股洪流带给大宋人民的到底是福还是祸?它将把大宋王朝往哪个方向引领?这一切,神宗和王安石也无法预料。此时,他们拥有的是任谁也不能阻挡的热情与决心。
经过一年的酝酿和准备,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再次升迁,由翰林学士而为参知政事,这是仅次于宰相韩琦的副相之位。王安石受命执政,雷厉风行,欲变风俗、立法度。神宗则视他为志同道合的知己,对他有求必应。制置三司条例司随之设立,作为主持变法的新机构,由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旭共同掌管。
一场在大宋朝绵延了整整十六年的伟大改革,由此正式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