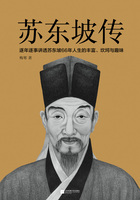
第5章 贤妻在侧,又识新友
仁宗驾崩后,韩琦出任山陵使,负责修筑皇陵,所需竹木依然由凤翔供应。
“编木筏竹,东下河渭”,为签判苏轼专职。早在一年之前与凤翔老校谈论衙前役之害时,苏轼就对这项差事的艰辛有所了解。尽管在他的努力下,已对衙前役的相关规定做了调整,但修筑皇陵重任在前,苏轼还是不敢有丝毫松懈。
凤翔地处西北,干旱是常态。这一年,不幸又遇旱灾,渭河干涸,沿岸的堤坝也已破败不堪,需要挖土修补,运送竹木之事变得尤其艰难。皇陵工期刻不容缓,木材必须在规定期限内送达。延误王事的重责,谁也担不起。
看到上千民夫拖着巨大而笨重的木材,在渭河泥泞的河床上艰难前行,苏轼的心情无比沉重。身为负责此事的地方官,他不得不一次次督促他们,他渴望天降大雨,以减这些劳苦人民的负重,可上苍这一次没再垂顾他们。
繁重的劳役搅得苏轼寝食难安,他奔波在凤翔的山间水畔,整个人变得又黑又瘦。最累的时候,他甚至想过逃离。不远处的终南山太平宫溪堂是多好的读书场所,在春日的鸟啼花香里,于溪堂深处捧书静读,是何等惬意。可也只能想想而已,明天还会有数不清的琐事等着他。
为皇陵集运木材的差事,苏轼足足忙了五个多月才算交差。
来凤翔后,与远在京城的弟弟苏辙鸿雁传书、写诗唱和,是苏轼消遣愁闷、寄托思乡之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坐在终南山太平宫溪堂里,听着窗外潇潇的雨声,一种难言的疲倦之意漫上心来。忙碌太久的人,一旦闲下来,大概都有过这种体验。
环境的艰苦,对苏轼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最让人难以消受的是那份憋屈。那时的苏轼,还不懂得太守陈希亮的苦心,他觉得自己在衙门里处处受挤对,回到家常常闷闷不乐,好在家里有位贤内助王弗。
王弗,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聪敏沉静、善解人意,与洒脱豁达、个性鲜明的苏轼正好互补。她十六岁嫁与苏轼。和苏轼刚成亲时,苏轼并不知道她通晓诗书,只见她终日不说话。苏轼读书时,她则拿着针线,静静地在一边陪坐。直到某日,苏轼读书“有所忘”,王弗竟准确无误地帮他接了下去,苏轼才知道妻子原来是个知书达礼的才女。
在凤翔那简陋的小院里,王弗整天做针线、理家务、照顾儿子。她虽年少苏轼三岁,却精明能干,又识大体,是苏轼生活中一位少不了的朋友与助手。
苏轼在外受了气,回来便会同王弗说,话里自然少不了陈希亮对他的种种非难。王弗总是含笑认真倾听,并时时安慰,叫他不必太过挂怀。有了妻子的陪伴与安抚,苏轼心中的郁闷自然减轻了不少。
苏轼天性热爱交往,和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朋友,还常常把朋友带到家里。他说话口无遮拦,旁边的王弗时时为他担着一份心。后来,王弗想出一个妙招,苏轼在前厅会客时,她就静静地站在屏风后,听他们交谈些什么,通过察言观色来判断苏轼所交之人的品行。王弗似有一双能洞穿世事人心的眼睛,她的预言一次次被证实,苏轼对她也越来越依赖。
说到交友,在凤翔期间,苏轼认识了三位朋友,这三人对他后来的人生路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不过他们的影响却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
彼时的苏轼,在工作中受尽陈希亮的气,却与陈希亮的儿子陈慥打得火热。
陈希亮有四子,最小的儿子即陈慥,字季常。他与苏轼的相识,说来颇有侠者相遇的味道。
那是嘉祐八年(1063)夏季,某天苏轼去岐山闲逛,密林丰草间,忽见三人骑马携箭,呼啸而来。他们正在密林间打猎,追赶一只疾飞而过的鹊。中间的年轻公子,尤其吸引苏轼的注意。大约嫌同伴太过笨拙,他怒马而出,拈弓搭箭,箭起鹊落,看得苏轼不由得喝彩惊叹。
那天,苏轼与他并马而行,谈古论今,也谈国事兵事,相谈之下,发觉彼此竟如此“臭味相投”。陈慥身上的豪侠之气,苏轼同样不缺少。二人遂成了终生莫逆。
对这个不思仕进,整日骑马负剑、游山逛水的小儿,陈希亮骂也骂过,打也打过,后来只好由他去。等到苏轼后来再在湖北歧亭遇到他时,他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此是后话。
治平元年(1064)正月,苏轼前往终南山,章惇听说后,携同僚一起从长安赶来拜谒。
章惇,字子厚,高大英俊,充满豪气,也博学善文,极富才华。嘉祐二年(1057),他与苏轼一起参加科考,并同中进士。然而,当他得知自己的侄子章衡高中状元后,因耻于官居侄子之下,竟负气而去。嘉祐四年(1059),他再次参加科考,高中进士甲科,才算出了口气。
章惇对苏轼,充满复杂难言的情感,羡慕、嫉妒、恨,合而有之。不过,此时二人还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纷争与利益冲突,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那段日子,他们同游同嬉,遍览当地山水楼观。
某日,二人来到一处名为黑水谷的地方。谷中有一潭,名仙游潭,潭上有南北二寺。苏轼和章惇原本是去游寺的,却被谷中的仙游潭吸引。万仞绝壁之下,林木掩映之中,怪石耸立,潭水深不可测,以绳缒下数百尺不得其底,以石投之,石入水中如片叶旋于风中,徐徐而下,好久才看不见。
章惇提出一个让苏轼震惊不已的想法,他邀请苏轼到对面的绝壁上题字留念。苏轼连连摆手摇头,章惇却是毫不含糊,他健步走到两绝壁之间的独木桥边,平步上桥,借一根绳索和壁上草木,摄衣而下,至一峭壁前,用事先备好的笔墨,在石上书了五个大字:“苏轼、章惇来。”再顺原路攀索而上。
整个过程,看得苏轼心惊肉跳。
再看章惇,却是面不改色气不喘。
“君他日必能杀人。”苏轼拍拍章惇的背说道。
“何也?”章惇不解。
“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苏轼回道。
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可想而知对待别人会如何狠心。多年之后,苏轼的预言不幸成为事实。不过,章惇高高举起的那把大刀,不是落在别人的头上,而是落在苏轼的头上。
送走章惇一行,苏轼还至岐山。在岐山下,苏轼又遇到了他生命中可称得上生死之交的朋友——文同。
文同,字与可,梓潼(今四川绵阳盐亭)人,与苏轼是西蜀同乡,还是苏轼的表哥。文同于仁宗皇祐元年(1049)中进士,苏轼曾赞他诗、词、画、草书为“四绝”,可惜他的草书早已失传,仅有四幅墨竹传世。苏轼曾跟文同学画,后自成一派,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大画家。文同曾对人说:“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
苏轼与文同的友谊,始于凤翔,绵延一生。
按宋代官制,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苏轼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抵凤翔任签判,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罢任。三年磨勘[1]期满,苏轼该回朝另候派遣了。
注释
[1]磨勘:当时官员考绩升迁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