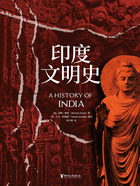
社群作为国家
自20世纪初以来,印度学家和印度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有一种政体,其令人生疑且总是出现在引号中,表达“共和”的意思。这些所谓的“共和国”,或称列国(janapadas),被更好地理解为“作为国家的社群”。在一些推算中,它们的存在时间为公元前800年左右到考底利耶(Kautilya)创作《政事论》的时代,通常认为是公元前4世纪。作为以氏族为基础的政体,从早期佛教的巴利语(Pali)资料和耆那教文本中都已发现了对列国的记载。其他资料,如《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政事论》和波你尼(Panini)的《八章书》(Ashtadhyayi),也都能为此提供佐证,并将调研的范围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西北部转移到东北部。
吠陀时期的列国和列国时期的十六雄国(mahajanapadas)(“大型社群”)很少是君主制的。根据夏尔马(R. S. Sharma)和其他一些古印度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些政权的社会关键是迦纳(gana),意为“部落”。夏尔马试图避免将迦纳简化为简单的血缘关系,而是选择将其理解为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之间的关联。对另一些人来说,表达这种形式的关键术语是僧伽(sangha),或合并的迦纳-僧伽(gana-sangha),但这些术语之间在含义上似乎没有显著的差异,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个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并可能于公元前800年左右已经存在。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特点是合议制政府:其主要成员部分是依据其出生于某个特定地方而被招募。因此,资格的获得,部分来自氏族的隶属关系和在族群应享的地位和财产的权利,其余的来自个人成就。在这样的政体中,或许某个人拥有罗阇(raja,即国王)的头衔,也许没有,但如果有的话,他的权力将受到议会的限制。
有一些非君主制的治理模式可以追溯到后来的吠陀时期的机构,称为萨布哈[4](sabha)和萨米蒂[5](samiti),这些被认为是后来吠陀时期耆那教派的著作中所称的“十六雄国”(Sixteen Mahaja-napadas)的模式。“Mahajanapada”有多种译法:王国、国家、领域和政治区域。然而,考虑到夏尔马之独树一帜的表述更具文采和更加深思熟虑,我更喜欢称其为“大社群”(great community),即这是一种人与属地的共同意识,其治理往往由成熟的和宗教上合法的合议机构实行。因此,我认为一个漫长的时代——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300年——是一个以社群为国家的时代。社群作为国家继续存在于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直到笈多王朝政权建立,直到那时,才出现了另一种不同的君主制形式,也就是社群和君主制同时形成了国家政权的基础,可以肯定这种观点与许多旧的以及一些新的学术观点是相矛盾的。
但我并非在暗示某种形式的社群停滞;社会形态不变的画面可能构成另一种“东方主义”的扭曲。例如,罗米拉·塔帕尔的著作中大量提及多种生产方式、分工、社会分层以及相当程度的城市化。正如查托帕迪亚雅(B. D. Chattopadhyaya)关于早期拉杰普特人(Rajputs)的作品所提醒的那样,这些情况一直持续到孔雀王朝建立起君主政体的宏伟秩序之后:根据他的论点,拉杰普特人中的王室血统在9世纪仍然在出现!
君主制的孔雀帝国与印度列国时代作为国家的社群有根本不同吗?从某种意义上说,答案是肯定的:阿育王的霸权言论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列国时代存在深刻差异。长期以来,他的铭文一直被解释为对一片辽阔领地建立起了统治。孔雀王朝的君王们,以及在他们之前的摩揭陀国王,确实刺激了印度南部国家社会的发展。然而,孔雀王国并没有成为后来国家的典范,这方面的成就应归于笈多王朝,笈多王朝充当了千年来国家的执政模板,通过这些模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界定印度的中世纪时代。
南部国家的出现是由公元6世纪帕拉瓦王国(Pallava)的建立开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恒河流域和地中海东部的对外贸易的影响。从印度南部铁器时代的巨石文化(megalithic)时期开始,并且明显地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后半期,发生了统治从乡村牧区高地向河岸平原转移的重大转变。与此相关的是,不同地区首领家族中的年长精英阶层的衰落,这些精英被新的精英阶层取代。在泰米尔人中,旧的族长被三个新的被称为穆文塔尔(muventar)的族系所取代,他们采用了朱罗(Chola)、哲罗(Chera)和潘地亚(Pandya)的名字,并建立了王国。泰米尔语桑迦姆诗歌(Tamil sangam)的文本中使用了“ventar”一词,意为“加冕国王”。这些王族不可能脱离以前在阿育王铭文中被注意到的世系结构,但他们一定基于复杂的定居农业社群,在南半岛的一些河流平原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即使它们保留了一些早期游牧社会和经济的要素。
北方王国继承了以血统为基础的吠陀文化后期的列国,其与后来出现的南方王国之间的差异,根据塔帕尔的描述,是源于这两个地区的不同环境和社会子结构。构成孔雀王朝中心地带及其在北部的继任者的核心族群是恒河流域的农耕村落。在孟加拉边境与恒河和亚穆纳河(the Yamuna)交汇处之间,单一的河岸延伸环境养育着同质的社群结构。相比之下,除河谷的某些地区外,大多数南部社群保持了定居耕种与牧业的平衡,这与特定地区生态型核心和周边地区一致;因此,定居点的单元也更加多变。另一个重要区别是海洋,以及先进的海上贸易,加上孔雀王朝入侵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后的侵入式商业,成为泰米尔纳德邦和卡纳塔克邦南部王国发展的催化剂。
虽然婆罗门宗教权威和印度教往世书(Puranic)的重新确立是南北共同的因素,但耆那教和佛教的命运在两个地区之间有着有趣的不同。笈多王朝时代的记载强调耆那教和佛教机构的继续存在,以及这两种信仰中重要著作的延续。此后,佛教与耆那教一起在孟加拉蓬勃发展了几个世纪,而在其他地方佛教则开始长期衰落,这部分是由于匈奴(Huns)入侵在西北部造成的破坏,部分是由于人们将佛陀作为化身纳入了毗湿奴的复兴崇拜。当时,包括皇室在内的一些大家族的佛教徒与毗湿奴派和湿婆教信徒之间通婚的做法也造成了佛教的衰落。
耆那教和佛教的和平更替与南方湿婆神的巴克蒂信徒对两者的暴力镇压形成鲜明对比:帕拉瓦王朝和潘地亚王国新国王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屠杀了耆那教教徒。这种说法令现代历史学家感到尴尬,但并没有促使他们做出解释。对这种暴力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可以集中在南部半岛商业和社群模式的不同构建方式上。耆那教连同佛教一起,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互动主义(transactionalism)思想,这是一种宗教传统,核心教义包括无神论和伦理道德,其节制和保守的社会习俗对商人具有吸引力。他们发现,由礼节守则约束的务实交往,比那些甚至是最虔诚的奉爱者的行为所伴随的放荡的社会交往规范和仪式更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
在卡纳塔克邦,耆那教作为一种主流宗教,享有长久的显赫地位,作为早期摩揭陀国和孔雀王朝贸易的遗产,其通过来自恒河平原的著名的达克希纳帕塔(Dakshinapatha)路线[6]传入,并吸引了相当多的王室赞助。这种商业联系在中世纪时期和之后继续发展,而恒河沿线商品继续进入南方。耆那教教徒在卡纳塔克邦的文化中找到了他们在6世纪后被泰米尔人拒绝的位置。
泰米尔人对湿婆和毗湿奴的崇拜中所进行的虔诚的实践和神学的采纳,实际上是一种发明,与帕拉瓦人新王朝的建立和旧穆文塔尔之一的潘地亚人的复兴是一致的。印度教的奉爱在这两个王国中都成为核心思想元素。其国王不仅通过建造神庙和赠予土地来敬奉往世书里的诸神,并慷慨地捐助他们和婆罗门祭司,他们还声称已经击败了一直忠诚于佛教的诸王。这种王室主张及其与国家形成的联系,展示出了复兴的印度教作为一种地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如上文所述,将耆那教和佛教说成是带有互动主义的思想是恰当的,那么将地方/领土视为奉爱崇拜的显著政治因素也同样是合适的。泰米尔人之间的社群结构与泰米尔人在公元6世纪后建立自己的宗教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信服的契合。
从那个时候到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后期,拥有土地的社群的组成是值得注意的。从前国家时代开始,聚居地就由各种生态区组合而成,从简单的高地/牧区与平原/农业到更复杂的,由河流或蓄水设施供水的大片湿润地区,与边缘地带有牧民的,干湿混合、农牧混合区域的组合。在少数地区,如高韦里河(Kaveri,又称科弗里河)、韦盖河(Vaigai)和坦布拉帕尼河(Tambraparni)流域的部分区域,灌溉栽培的扩展延伸区域非常整齐划一,并有局部复制类似恒河流域数字聚类做法的可能性,但那是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社群认同是通过宗教信仰,通过供奉特定神祇的寺庙而在文化上构建的。神祇受到特定区域的部族的敬奉拜谒,包括他们的族长,他们可能是大族群部落下按等级各自分管各自的领地的。对寺庙的敬奉和资助,以及涉及社群、商业和国家政权形成的相关进程,为中世纪早期社会奠定了基础,其中出现了新的社群和国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