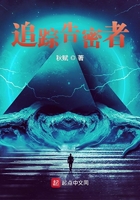
第40章 ?桃粉红的盐
我拿了一个盐瓶给餐盘里的汤加了点盐,耳边仿佛响起了这样的歌声:
“桃粉红的盐巴
神女的面纱
越过九十九座山
跨过九十九个海子
赶着我的黑牦牛和老山羊
手持木铲的阿帕巴啦
不要只铲上层的盐
木架下的冰挂挂
才是神女的发簪”
在升腾的热气中,我给柴灶加了把柴火,用嘴巴往里吹气;向阳花在炒细沙,她唱着一首歌谣,锅里的温度一直在上升。
这是炒青稞的前戏:
先用大炒锅把沙子炒烫,向阳花抓起一捧洗净的生青稞,放进炒锅细沙堆里,两手持木柄,端起锅,用力颠着炒锅。刹那间,滚烫的沙子与青稞相碰撞,发出劈劈叭叭的声音,就像过年放鞭炮,脆生生此起彼伏,多次颠炒后,声音小了,她迅速将这一锅倒入筛子里,将沙子筛回炒锅,筛里剩下一堆咧着嘴“笑”的熟青稞。
我试着想学会这个技术,她放手让我学,一会儿不是烫了手,就是炒糊了,只好都丢给小黑吃了。
我把炒好的青稞,放在木桶里,送到村里的水磨房,磨成糌粑。
水磨房在河边,蓝色的房顶上插着五彩风马旗;上面挂着清脆的铃,叮叮铛铛响,水磨出来的就是新鲜的糌耙。
将它与酥油混合着吃,清香无比,这饱含着丰富营养的食物,给了我们初冬季节全部热量。
我问向阳花:
“雪域人家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她指了指灶台上挂着的一排擦得铮亮的铜锅、铜勺等厨具,看到我疑惑的眼神,她坚定地点点头。
她理解为家庭中最急需的餐具了。
我又问:
“雪域人家中最稀罕的是什么东西?”
“桃粉红的盐巴”。
她的回答者是与生存有关的物质资源。
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在雪域吐蕃王朝之前,盐的确是比金子还要贵重的生活必须品,向阳花説的桃粉红色的盐,只产于澜沧江上游,十分珍贵,是盐中的爱玛仕,去往采盐的路上,途中千山万壑,只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过,山路临着悬崖绝壁行路,宽度只容一人通过,胆小的马,只要看一眼山下的悬崖就会腿软而翻到山下。
因而盐井就成了兵家必争的战略物资。
盐田之争在雪域的历史中十分常见,最有名的就是格萨尔王与纳西王羌巴之间的“羌岭之战”。
可见向阳花回答的并不错。
在她的眼中,父亲的活计是多么的重要。
“一年有四个季节
别人家的阿帕巴啦出去背盐
留下了两个季节在家
但我的阿帕的盐怎么也背不完。”
每每说到父亲,她的脸上露出神圣的光芒,仿佛背盐是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桃粉红的盐巴
只喂我的小花马,
羊羔也可以舔一口
出发的牦牛
才能在路上舔舔盐袋
可怜的老山羊
驼着它刚到家就倒下。”
看来桃粉红的盐巴是深受牧民喜欢的盐,能让牲畜变得更强壮。
向阳花的歌谣还一直停留在童年时期的记忆里。
我让小孙当翻译,我把这些歌谣写下来,寄给了BJ民院的老师,让他指出这里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有价值的东西,我想如果有线索,一定会在歌谣中出现。
我收到了第一封信是拂晓写来的,致以同事般的问候,知道我的去处安了心,并告诉我韦凌云经过中医的治疗恢复迅速,应该很快会好起来,可能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恢复了原来的记忆,这个消息让我振奋。
我把这个消息赶紧告诉张乎,也让他催一下民院老师对这批歌谣的分析,我在信中的结尾署名是诗人宋明,告诉他千万不要透露我的身份,就当我在当地采风,免得影响老师的判断力。
不久民院老师给了回信,在信中大大夸我做了件好事,收集了几近湮灭的驮盐歌谣,但是又奇怪地问,一般驮盐女子是不能参加的,为何一个女子知道那么多?
当然他们不知道向阳花识字,一直住在寺院中,每每她的父亲回来,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哼唱起这些歌,对于一个思念父亲的女儿来説,肯定会用心记下来父亲的歌谣。
接下来老师给出的答案让我不淡定了:
一般驮盐人只有两季外出,为何歌谣里的父亲四季都在驮盐?这个驮盐人不同寻常。
我一边干活一边问向阳花:
“为啥阿帕巴啦四季都外出驮盐,丢下孤苦的你?难道他不是一看才出去驮两次,像其它人一样?”
“粉红色的盐啦,它是最珍贵的啦。”向阳花答非所问,回避我的问题,这证明了我的判断:
她知道通道在哪,并知道心中最珍贵的粉红色的盐是什么。
我给拂晓又发了一封信,写下了我听向阳花唱的歌谣,我想我现在作为一位游吟诗人,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品味到诗的真谛,它是真,是善,是美,是语言的盐,也向她表明:我正是草原上创作,让她安心。
不久,关于我对卡城草原驮盐歌谣的思考,拂晓给发了一整版,不仅在县里的报纸,在w市报的副刊,包括其它的能有副刊的平面媒体,拂晓都替我转发了,一时间稿费汇款单像雪花一样飞到了达娃的手里,他惊讶地发现:
卡城草原上来了一位伟大的游吟诗人。
我感激拂晓的推荐,我真的太需要这些钱。我把它们全部转给老朱订了春茶,本来这笔钱是想从龙龙这儿取的。
老朱説广东的老板追加了明年的茶叶订量,如果我的预付资金跟得上,这是一笔大买卖,我回答説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会有钱的,让他稳住后山的茶农,只是他不理解,我为何跑到老大远的,一边写诗,一边收款,很多年后,他説从没想到我白天做商人,晚上是诗人。
达娃次仁等到我后,先让我读着报纸上的我写的诗,一边听一边点头,也不知道他听懂了多少,在对我的诗歌崇敬中,达娃次仁没有坐在家中看守着邮包和电话,他骑着一匹老马上路了,小店由他的女人接过来看着。
在藏民眼中,一片写字的纸都是神圣的,如果在路上发现了,都要捡起来带回家收好,何况我送了他十多张报纸上我写的文章呢,仅管他看不懂。
我问女人,达娃沿着哪条路走的?
她指着高高的格聂雪山上的道路説:
“茶马古道”。
在更早的年代,这条道路是一直通往前藏的茶马古道,从雅安等地驮来的茶叶,在这儿打尖,然后再去往LS,达娃家就是当年的驿站,为过往的商旅提供粮草,送达信件。
数百年来,百年藏寨是这条交通大通道上的重镇。
因此我确信,他一定会找到玛吉阿米,以他的百年驿站世家为保证。
想到这,我对龙龙説:
“快了,最多一个月,达娃就能找到她,放心,她会跟着我们回香格里拉。我们现在做好回家的准备吧。”
我想象着未来的某一天,龙龙骑着白马带着玛吉阿米,我带着向阳花和小孙,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从布达拉朝圣回来一样,重返香格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