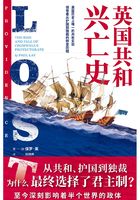
第二章:新旧世界
我们英国穷吗?西班牙倒是很富有,因为他们有我们的西印度群岛。
——约翰·艾略特爵士,1624年3月
托马斯·盖奇过着他那个时代英国人最不平凡的一种生活,在这期间,他的政治观和神学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盖奇出生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宗教反叛长久以来一直抗拒英国国教的家庭,他的父母都因窝藏天主教神父而被判死刑,后来改为缓刑。他的一个叔叔因参与1586年巴宾顿阴谋而被处死,这个阴谋计划暗杀伊丽莎白一世,把查理一世的祖母、苏格兰女王玛丽扶上位。耶稣会殉道者罗伯特·索斯韦尔则是他的堂兄。
盖奇在大概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法国北部圣奥梅尔天主教神学院学习,那里是英国国教反抗者最聪明子女的默认目的地。他的父亲想让他加入天主教耶稣会,耶稣会修行严格,精英荟萃,其因殉道者埃德蒙·坎皮恩16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教运动而在英国臭名昭著。但是,盖奇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而是去了更远的西班牙,进入巴利亚多利德的英语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加入了多明我会,这是一个成立于13世纪的古老教派,同样致力于高等教育。正是因为这一举动,父亲与他断绝了关系。
作为一名英国人,盖奇被正式禁止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室领地内旅行,尽管如此,生性就不安分的他禁不住自己那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的诱惑,钻进一个干饼干桶里(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偷偷登上了停靠在加的斯港的一艘船(从某些或许是虚构的描述来看,盖奇当时很有可能过度沉迷于赫雷斯非常有名的葡萄酒)。这艘船是驶往墨西哥的,到了墨西哥,他本应该开启下一步前往西班牙属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旅程,但这个转乘并没有发生。相反,盖奇(现在,他已改名换姓叫托马斯·德·圣马里亚,他将和一小拨儿多明我修士前往他的“第二祖国”危地马拉,接下来的十年,他将在那里度过。盖奇在学习语言方面非常有天赋,他混迹于玛雅族博克曼人中间,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他们的语言。一路走来,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否正确。他承认,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困惑与动摇”。
1637年1月,随着英国人向普罗维登斯岛拓殖接近混乱的尾声,盖奇开始了一段漫长而危险的返回欧洲之旅。在莫斯基托斯海岸现在叫伯利兹的地方被荷兰海盗打劫后,他一路穿行到达中美洲地峡的太平洋一侧,然后从那里坐船向巴拿马出发,最后到达西班牙大陆美洲的重要港口波托韦洛港(据说弗朗西斯·德雷克1596年因患痢疾病逝后就葬在这片海域)。在这里,盖奇将自己登记成为把他送回西班牙的船长的神父。由于母语已经被他忘得差不多了,1637年,盖奇隐姓埋名来到英国,秘密回到了他出生的反抗者之城。在这之后他又去罗马游历,躲过法国海盗的魔爪后,于1640年再次回到英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盖奇皈依了英国国教的清教徒一派,他说自己之所以改变信仰,正是因为受到“长期议会”承诺的宗教改革的激励。1642年8月28日,盖奇在一篇布道词中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改宗,这篇布道词后来以《在一个改宗罪人的眼泪中发现的撒旦暴政》为名发表——盖奇可不是一个低调行事的人。议会对盖奇的举动深感满意,随即派他到肯特郡的一个教区主事,那时他已经结婚,这可以说是宗教改革运动赐予的毫无争议的祝福之一了。当然,这只是个前奏,更重要的职位还在后面,接下来他将到肯特郡迪尔港的圣伦纳德教堂任职。
在那里,他出于自辩,完成了自己扣人心弦的游记——《英裔美洲人:他的海陆艰辛之旅》,又名《西印度群岛的新考察》。1这篇游记最终于1648年在英国出版,并在标题页注明“谨以此书献给托马斯·费尔法克斯”(费尔法克斯是内战期间带领议会军大获全胜的统帅),这么做无非是想获得进一步的提携。这本书不仅是第一次以英国人的眼光来描述西班牙新世界的生活,而且也是第一次由非哈布斯堡王朝臣民来写这样的主题。
甫一出版,《西印度群岛的新考察》就荣登畅销书榜单,虽然书中到处都是长得喘不过来气的段落,但可读性却出奇的好。食物可谓盖奇最喜爱的话题,这无疑是因为他忍受了太长时间的困苦。他第一次用英语描写了墨西哥的经典菜品,比如墨西哥面卷(吃的时候“先蘸一下水和盐,再加点青椒”)和墨西哥玉米粽,而对那些为他们准备食物的印第安人,他的笔调也是感人至深且充满同情心。看起来他好像还发现了玛雅族博克曼人用有毒的蟾蜍泡酒,他们在宗教仪式上就喝这种酒求醉,以增加性能力。盖奇用了一章的篇幅写巧克力——“他们用一品脱以上容量的大杯子装巧克力,用来招待客人”。他对这种黑乎乎黏稠的调制食品很感兴趣,尽管他预感到“大量食用这种巧克力会让人变得又肥又胖”。盖奇的游记有一个特点,书中时不时就出现讽刺宗教的段落,比如他提到了一个天主教神父的故事,讲的是这位神父在做弥撒时,一只老鼠跑进来把圣餐饼给叼跑了,于是他不得不放弃仪式。
盖奇的性格也有不讨人喜欢的一面,这在内战期间暴露了出来,当时他积极地站在议会一边。盖奇出庭作证指控他的三位前同僚,分别是:托马斯·霍兰德,盖奇是在圣奥梅尔学习时认识霍兰德的,这位神父于1642年被处决;亚瑟·贝尔,他是盖奇一位表亲的随行神父,一年后因叛国罪被处死;第三位是盖奇在1651年指控的彼得·赖特,赖特是他哥哥的随行神父,他哥哥名叫亨利,为保王党的一名骑兵军官(亨利“努力消除对托马斯的所有记忆”,最后死在赖特的怀里)。最恶劣的还要数盖奇指控他的弟弟乔治,乔治也是一位神父,毫不令人意外的是,乔治给盖奇下了定论,说他是个“不光彩的兄弟”,他的所作所为“让我们全家人感到羞愧”2。
1654年,盖奇发表了一篇名为《对锡安和巴比伦的全面调查》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改宗者无限狂热的态度捍卫了护国公制的政治与宗教抱负。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弑君者托马斯·查洛纳的怂恿下,盖奇向克伦威尔的间谍头子约翰·瑟洛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西印度群岛的一些简要如实观察”的报告,建议英国人远征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心脏地区。据威尼斯共和国驻英国大使弗朗西斯科·贾瓦利纳讲,盖奇和护国公克伦威尔曾多次私下会面。这绝对是一个对未来影响深远的行动,用历史学家大卫·阿米蒂奇的话说,它将成为“英吉利共和国重现帝国时期荣耀”的奠基石3。此举将导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覆灭,同时给教皇制蒙上怀疑和不确定的阴影,最终让其彻底失败。
*
在这份报告中,盖奇摆出若干理由,他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及从更广泛意义来说的教皇制,这两者的实力几乎完全建立在掠夺新世界帝国殖民地资源的基础上。盖奇断言,它们的财富和帝国强权蕴藏在它们的“美洲矿藏”里。如果它们失去了这些矿藏,“罗马教宗的三重冠很快就会从神坛跌落并腐烂”。
靠着卖弄教皇党人的陈词滥调,再掺和上约翰·福克斯的殉教传记,盖奇在狂热的新教徒和反西班牙者中收获了不少拥趸,其中就包括克伦威尔。盖奇斩钉截铁地说:“西班牙人扛不了多久,他们懒惰而邪恶,像野兽一样中饱自己的贪欲,贪婪地蚕食着肥沃的土地,从来没有受过战争的训练。”4盖奇的这番言论狂妄至极,凭一己之私鼓动克伦威尔的反天主教主义,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话竟然出自一个曾近距离看到西班牙帝国主义虎口獠牙之人的口中。但盖奇只给出了部分关于英国顺承天意和西班牙吓得心惊胆战的谣言和预言:“西班牙人自己早就开始疯传,从某些迹象来看……一个陌生的民族将打败他们,夺走他们的所有财富”。
这样的预言并非空穴来风。1623年,白金汉公爵——第一世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是詹姆斯一世的宠臣,后来又和国王的王位继承人打得火热——乔装打扮一番后陪着未来的查理一世踏上注定没有什么好结果的马德里之旅,他们此行有个异想天开的计划,那就是向西班牙腓力四世的女儿秘密求婚。查理求爱失败,但却爱上了欧洲的艺术品,于是用船疯狂地往英国运送收集的艺术品。在马德里,一位名叫“唐·芬恩”的西班牙官员告诉白金汉公爵一个印第安人的传说,这个传说预言:“未来将有一个民族来到这里进行统治,他们发色淡黄,皮肤白皙,眼睛呈灰色。”5谁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解放者呢?他们是“唐·弗朗西斯科·德拉科”——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继承人,他和沃尔特·雷利一起为反西班牙的“黑色传奇”拾薪添柴,让世人了解西班牙人在新世界的残忍和剥削行径。按照这种说法,西班牙不仅是英国的宿敌,而且还是“监护征赋制”j的一手缔造者,让新世界的土著人民深受剥削和压迫。西班牙恶毒的形象以及人们对这种说法的接受,又因为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英译本作品的出版而在英国人心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部著作名为《西印度群岛毁灭述略》,书中形象地描述了西班牙对美洲土著人民的暴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盖奇指出,这本书之所以引发这么广泛的关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折射出1641年爱尔兰叛乱期间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定居者遭受的暴行,教皇党人的类似作品对此进行了记述,虽然几乎总是存在夸张的成分。盖奇认为,“圣克里斯托弗岛、圣马丁岛、普罗维登斯岛……托尔图加斯群岛的英国人已被西班牙人驱离,那里的英国人受到西班牙人最不人道和最野蛮的对待”,我们英国人复仇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如果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取得海外战争的胜利,就能在军事威力的彰显中让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团结在一起。
*
克伦威尔上台之际,虽然普罗维登斯岛公司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留存的记忆仍然激励着新统治阶级的成员。普罗维登斯岛公司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公司的规模不大,资金有限且全部来自私人投资,而且没有和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试想一下,如果这个计划在背后能得到国家资源的全力保障,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又有谁能挡住英国向海外拓殖的步伐呢?
克伦威尔赞成沃尔特·雷利在《世界史》(这或许是克伦威尔唯一读过的除《圣经》以外一本书)中表达出来的观点,即新生的英吉利共和国应树立伊丽莎白时代那种放眼世界的帝国主义思想。克伦威尔让他的儿子理查德谨记这种思想,因为“历史是造物主、上帝的意志和神圣的天意创造出来的”6。这种观点在《名人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生平》一书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与升华,这本书表达了对“基督教的斗士、完美的英雄骑士”的礼赞(这位英雄人物指的是诗人约翰·弥尔顿,他是新成立共和国的批判性友人,被誉为“比苏格拉底和阿奎那更好的良师”)。此书由第一世布鲁克勋爵、普罗维登斯岛公司最年轻创办人的养父富尔克·格雷维尔于17世纪10年代写成,直到1652年才出版。书中主张对西班牙应采取进攻性的积极外交政策,得到了现政府支持者的首肯。在内战过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悲痛时分,兜售安全、抚慰和爱国主义怀旧情调的出版商发现,重新出版德雷克和雷利探险的书籍有利可图。
克伦威尔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征兆。在他与大西洋彼岸波士顿神学家约翰·科顿的通信中,这位圣经学者试图解答护国公提出的下列问题:“上帝的所行所为是什么?”“什么预言正在实现?”科顿劝告说,如果克伦威尔打算攻打新世界的西班牙人,他会“让幼发拉底河干涸”,他说话引用的是《启示录》中的一段话:“第六位天使接着将他碗中所有的倒在幼发拉底大河里,河水立刻干涸,便为东方各国的王预备了向西入侵的道路。”这个比喻并不是很恰当,克伦威尔更感兴趣的是让向西班牙运送新世界财富的“幼发拉底河”改道,流到英国的地盘上,把西班牙架空,任其干涸下去。尽管如此,这个不完美的形象还是留下了。
断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财路将推动西班牙政府走向破产,削弱西班牙的军事实力,同时还能充实护国公制英国政府的国库并清偿其债务。除此之外,通过斩断向教皇提供支援的“后盾”——克伦威尔就是这样描述西班牙的——英国新教教义的千年王国梦想就将得以实现。这种执念在克伦威尔对犹太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期许中也显露无遗:他渴望让英国重新接纳犹太人,以实现圣经的预言;他还把美洲印第安人幻想成消失的以色列十支派之一,据说他们的先辈会说希伯来语。他们被认为以后将反抗西班牙人,因此是英国对抗西班牙的潜在盟友。
克伦威尔组建的政府对外正逐渐树立起实施宗教宽容政策的声誉,至少以17世纪的标准来看是这样的,尽管这个政府的法律条文将否认基督神性的人排除在外,正如克伦威尔将于1656年9月17日在第二届护国制议会发言时表明的那样:“我要向你们坦言,从上届议会的施政来看,它是想让全国人民看到,无论怎样标榜宗教,只要他们不把宗教当作动武和流血的借口,而保持缄默与和平,他们就可以享受良知与自由带来的快乐。”
让犹太人返回英国是克伦威尔的个人倡议,而力促英国重新接纳自己族群的犹太人代表,则是一位葡萄牙裔拉比k兼作家玛拿西·本·伊斯雷尔。1652年,他的著作《应许之地以色列》被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发行,书名叫《以色列人的希望》,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在英国特别受欢迎。本·伊斯雷尔特别渴望能为犹太人找到一处庇护之地,当时犹太人正在俄国忍受新一轮的迫害。1651年,就在克伦威尔盘算着重新接纳犹太人能带来哪些宗教与世俗利益之际,伊斯雷尔在阿姆斯特丹与瑟洛会面。这位英国国务大臣将大量涌入的有关欧洲事务的新情报(这些情报可能来自犹太人的关系网)反复梳理,然后召集人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就本·伊斯雷尔提出让犹太人到英国定居的申请以及他本人于1655年抵达英国进行磋商。克伦威尔盛情款待了本·伊斯雷尔,并将他的住所安排在靠近白厅行政中心的斯特兰德大街。但是,本·伊斯雷尔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解决犹太人重返英国以及与英国公民享有同等的自由贸易权利问题,他还要求英国赋予犹太人公开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允许犹太人死后葬在自己墓地的权利。克伦威尔的国务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专门研究本·伊斯雷尔递交的请愿书,当然,这个委员会对伊斯雷尔的请求颇为冷落。此外,法官、教士和学术界人士也共同召开会议,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克伦威尔为了支持犹太人重返英国,在议会作了一番非常有说服力的陈词。虽然犹太人重返英国有着非常明显的商业吸引力,但克伦威尔的基本出发点主要还是宗教方面的考量。根据预言,只有犹太人改宗,才能实现地上的基督国度,而这个加速建立基督国度的机会就摆在面前。通过努力教导国人信仰真正的宗教,英国将成为最有能力向犹太人揭示真正宗教的国度,这是因为,克伦威尔认为英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用最纯粹的宗教来教导人们信仰的地方”7。虽然有些人仍然认为犹太人因杀死了基督而该受到永世的诅咒,但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做,当委员会把讨论议题公之于众时,显然可以看出,英国民众的反犹主义还是根深蒂固。当然,真正的反对来自商人阶层,他们对犹太人的经商能力、经验和关系网心存恐惧(从古至今都是这个世俗的理由)。然而,克伦威尔是不会站在拒绝新的资金来源立场上的。
1290年,爱德华一世凭借君主特权将犹太人驱逐出英国,因此,遵循先例,他们同样也可以在护国公的特权下重返英国。出席委员会的两名法官找不到任何正当理由反对英国重新接纳犹太人,因此,克伦威尔抛出了口头协议,坚决支持犹太人重返英国,针对天主教徒不服从国教的法律不适用于犹太人,犹太人可以购买墓地。新的犹太教堂位于笼罩在伦敦塔阴影之下的克里教堂巷,虽然有时也会提心吊胆,但犹太人还是开始在这里公开做礼拜。虽然克伦威尔从未正式颁布重新接纳犹太人的法令,但1656年通常被视为犹太人重返英国的日期l。
克伦威尔的外交政策含有很明显的道德成分,几乎看不出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他曾经试图与荷兰人结成新教联盟,这引起了他的潜在盟友和教友国家的恐慌。他与葡萄牙人谈判,为英国商人谋求在里斯本的贸易权(以及新教信仰权),以此进入利润丰厚的巴西市场。但是他的外交政策最看重的是“两顶皇冠”,即法国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黑化”的西班牙希望与英国结盟一起对抗法国,同时又担心英荷海军再度联手——这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西班牙挥之不去的噩梦。在马德里,没有人愿意看到“两个共和国的舰队共赴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因为荷兰也与法国结盟。
和西班牙相比,法国首席大臣枢机主教儒勒·马扎然制定的外交政策显得更为老练而明确。1652年,马扎然派特使安托万·德·波尔多·纽夫维尔抵达伦敦,当时克伦威尔正挑起法国西南部胡格诺派中的内部争端。1652年以来,英国一直处于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m的战事之中;一旦这场第一次英荷战争结束,不仅西班牙人头疼,法国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唯恐游荡在英吉利海峡上无所事事的英国舰队找法国麻烦。从私下的关系来看,和波尔多相比,克伦威尔和西班牙驻伦敦大使阿隆索·德·卡尔德纳斯走得更近,马扎然对此心知肚明,他需要怂恿英国认识到,西班牙而不是法国才是英国的宿敌,这种观点被英国清教徒广泛接受并深以为然。法国外交官让-夏尔·德·巴斯奉命向克伦威尔表明这一点:西班牙占领的西印度群岛才是克伦威尔的海军最容易得手的目标,而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盖奇的观点。
英国军队是一支久经考验的军事力量,其保持欧洲势力平衡的能力可谓日益增长。克伦威尔将西班牙和法国玩弄于股掌之中,让两国陷入对立状态。他告诉卡尔德纳斯,只要西班牙肯拿出一百二十万英镑,他就会派出三十艘军舰和两万名士兵,在佛兰德斯与法国开战。卡尔德纳斯的出价不超过三十万英镑,对这个开价,克伦威尔表示他可能会考虑组织一场封锁战,仅此而已。但是,当他明显感觉到卡尔德纳斯连三十万英镑都拿不出来时,这位护国公便提议,要是没钱,让出领土也可以接受。如果西班牙能将敦刻尔克港割让给英国,虽然和谈妥的价格相差不少,但他会因此同意向佛兰德斯派出海军和陆军。卡尔德纳斯接受了。
与此同时,克伦威尔向法国也抛出了类似的承诺,如果能从法国那里租借布雷斯特港——这处港口显然比敦刻尔克港更诱人——而不是从西班牙人手中永久获得敦刻尔克港,他就将派兵支援法国在佛兰德斯的部队。这可谓典型的既阴险又狡诈的伎俩,时人无出其右者。
西班牙议会拒绝了克伦威尔关于敦刻尔克港的提议(尽管卡尔德纳斯此前表示赞成);法国在与克伦威尔打交道时表现得更为强硬,压根儿就没把租借布雷斯特港列入讨论议题。西班牙卷入了佛兰德斯、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的冲突。法国在马扎然的得力指挥下应对自如,根本谈不上不堪一击,可动用的资源也没有那么捉襟见肘。
克伦威尔和他的国务会议认为,与法国开战“胜算不大,而且无利可图”。如果采取削弱法国(法国的高卢派教会对罗马教廷完全独立自主)和“扶持”西班牙的政策,这将对“整个欧洲的新教事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在克伦威尔恢复伊丽莎白时代荣耀的世界观里,西班牙一直都是“全世界新教徒的最大敌人……也是横在英国迈向巅峰之路的宿敌”。未来“很麻烦”,特别是将不可避免地蒙受对西班牙贸易的损失,包括利润丰厚的毛呢出口,兰伯特对此尤为在意,因为他的家乡约克郡是英国毛纺业的中心。但是,与法国媾和的重要性远超这些损失,如果能缓和法国对英国的敌意,就不太可能让法国与相对平息的苏格兰重新结成“老同盟”n。
开弓没有回头箭。国务大臣瑟洛告诉保王党人、第一世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卡尔德纳斯曾这样警告他说:“想废除西印度群岛的宗教裁判所并取得自由航行权,你得先问问主人答不答应”。8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这么说可看成是西班牙向英国挑衅的又一个例证。有人会说,为了迎合公众,推行反西班牙政策——这一政策将发展成为未来的远征西班牙西印度群岛殖民地计划——将被视为政府对诸如此类蔑视的报复,而不是先发制人的打击。
注释
j 监护征赋制是西班牙王室在美洲进行殖民活动时用来管理和统治印第安人的一种主要的法律体制。在监护征赋制下,西班牙王室授予个人强迫印第安人劳动和收取金银或其他物品的权利。实际上,监护征赋制和奴隶制别无两样。许多印第安人被迫去做高强度的劳动,如果反抗的话,将会面临极其残酷的惩罚甚至死亡。
k “拉比”是犹太教宗教领袖,通常为主持犹太会堂的人、有资格讲授犹太教教义的人或犹太教律法权威。(译者注)
l 英国的犹太人对克伦威尔的看法往往与爱尔兰人截然不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并不是唯一一个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奥利弗”的犹太人。
m 俗称“荷兰共和国”。(译者注)
n 老同盟,是指欧洲中世纪时期苏格兰与法国之间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针对英格兰的同盟关系,包括一系列攻击性和防卫性的双边条约。同盟开始的标志是1295年10月23日在巴黎签署的条约,历经周折,直到1560年的《爱丁堡条约》才终止了两个国家之间特殊的、持续时间长达二百六十五年的同盟关系。该同盟曾被戴高乐将军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同盟。(译者注)
注释
1.Thomas Gage, The English-American: A New Survey of the West Indies1648 (El Patio, Guatemala, 1928).
2.See Allen D. Boyer’s entry on Gage 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National Biography.
3.See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 1996).
4.Thurloe State Papers, vol 3, p. 60.
5.‘The Secret Discovery which Don FENNYN, a Spanish Secretary,made to the Duke of Buckingham, in the year 1623, at Madrid’, Clarendon State Papers, vol. 1, p. 14.
6.Hugh Trevor-Roper’s review of Christopher Hill’s Intellectual Origins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in History and Theory, 5 (1966), p. 77. I am indebted to Blair Worden for this observation.
7.Quoted in Peter Toon, God’s Statesman: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Owen: Pastor, Educator, Theologian (Eugene, OR, 1971), p. 37.
8.S. R. Gardiner, Oliver Cromwell (London, 1901), p.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