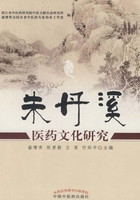
一、文化渊源探讨
朱丹溪文化渊源
(一)元代金华理学家许谦对丹溪的影响
许谦,字益之,晚号白云山人。婺州金华人。学者称白云先生。《元史》有传。
许谦天资高嶷,五岁就学,庄重如成人。宋亡家毁,年幼即孤,而力学不辍,借书昼夜苦读,虽疾恙不废。年过三十,开门授徒。闻金履祥讲道兰江,乃往就为弟子。时金年已七十,门下弟子数十人,许谦独得器重。居数年,得师所传朱熹之学,油然融会。金殁后,许谦专事著述讲学。地方官闻名屡荐,皆不应,屏迹东阳八华山中,学者负笈重趼而至,著录者前后千余人。许谦教人,至诚谆悉,内外殚尽。尝曰:己之有知,使人亦知之,岂不快哉!为教凡四十年,“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朱子之大至许公而益尊”,对程朱理学的发扬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许谦及其上三代宗师——何基、王柏、金履祥,在金华地区递相授受朱熹理学,是金华理学的主要传人,史称“金华四先生”,亦称“北山四先生”。《元史》载:“何基、王柏、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嫡。”所以,元代金华理学号称朱学嫡脉,而许谦被称为金华理学大师。卒后十年之至正七年(1347),赐谥曰文懿;所著有《读书丛说》《读四书丛说》《白云集》及《诗集传名物钞》等。
丹溪师事许谦,确是人生的转折点。许谦为之“开明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丹溪“日有所悟,心扃融廓”,由此苦读默察,见诸实践,严辨确守理欲诚伪之消长。“如是者数年,而其学坚定矣。”《宋元学案》引宋濂说,认为“其学以躬行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为礼乐之原,积养之久,内外一致”。自此之后,丹溪处事行世,待人接物,著书立说,率以理为宗;丹溪援理入医,理学亦成为丹溪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丹溪弃举子业而致力于医,固然有赴考再往再不利的经历,也有“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的动机,更有许谦的直接劝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弗能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丹溪听从许谦言而坚定了从医的决心。所以,许谦对丹溪的影响是全面的,思想、方法、道德、行为、经历等无不留下许谦或者说理学的深刻影响。
《格致余论·倒仓论》尚留丹溪治疗许谦的医案:“吾师许文懿始病心疼,用药燥热辛香如丁、附、桂、姜辈,治数十年而足挛痛甚,且恶寒而多呕,甚而至于灵砂、黑锡、黄芽、岁丹,继之以艾火十余万,又杂治数年而痛甚,自分为废人矣,众工亦技穷矣。如此者又数年,因其烦渴恶食者一月,以通圣散与半月余而大腑逼迫后重,肛门热气如烧,始时下积滞如五色烂锦者,如桕烛油凝者,近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而略思谷,而两足难移,计无所出。至次年三月,遂作此法(指倒仓法),节节如应,因得为全人。次年再得一男。又十四年以寿终。”
许谦卒于至元三年十月,当时呼子许元受遗戒,“门人朱震亨进曰,先生视稍偏矣,先生更肃容而逝”。此可见许氏理学家的“静定”功夫,亦可见丹溪侍奉许氏的恭敬态度。
(二)家学渊源
赤岸朱氏诗书传家,簪缨相望,为当地望族。自宋以来,尤崇尚理学和医学。宋濂说:“朱聘君家世习儒,至聘君始以医鸣。”据《赤岸朱氏宗谱》所载,丹溪家世中以儒理之学著名者有:
从曾祖朱杓,“天性刚直,平生一语不妄,博洽群书,不应科举”,“从徐侨上承晦庵之绪,精究理学,著《太极演说》《经世补遗》等书”。对道与体、知与行、常与变等哲学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其论道与体,“道体虽一,用则万殊,而体用各具一物之中,此道之所以流行不已也”;论知与行,则谓“知之明则守之固,守之固则行之力,行之力则智愈明,此是知行并进,圣门之学,莫切于此”;论常与变,则谓“鹤鸣九皋,声闻于野,言微之显也;鱼潜在渊,或在于渚,言常之变也”。“(朱杓又)幼抱羸疾,访览医书,慨然曰,与其疗一己之疾,莫若推以及人……而汇药以应病,祖述《本草》《千金方》意论,集其已验者曰《卫生普济方》,采摭经传格言冠于篇端。须江徐公为之序曰:‘是书不唯拯人之有疾,且欲导人于无疾。’”其理学和医学造诣对于丹溪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
从曾祖朱锷,深究理学,亦兼通医学。所著《自省篇》多以理言医内容。如所言:“清心寡欲,以为养寿之基……人于暮年,精力尤宜爱护,譬如灯火,若置之风前而频施挑剔,是速其灭也……不独暮年如此,虽于壮健之时,若不能内节七情,外顺六气,曲尽保养之道,将见东补西漏,左扶右倒,救疾之不暇,尚何望其强毅果敢,充此精力于一身?”又言:“动者静之始,静者动之基,此理互为根,动静常相随”;“省虑以养神,省言语以养气,神不上驰,气不上耗,则心肺之精上交于肝肾;脾居中州,运水谷之精,为心肝肺肾之养,以取其交,故能生血以养筋,生精以强骨,生肉以充形;形体充实,筋骨强壮,则苛疾不起”。这对于丹溪医学思想尤其养生观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可以说,朱丹溪援理入医,将理学结合到医学中来,以说明医学问题,家族的影响确不可忽视。
从祖朱叔麒,宋咸淳四年进士,历尹定海、仙居,同知黄岩、浮梁二州事,仕而兼通医学者。“其在官,狱囚有疾,必治善药,亲临饮之;其在家,储药于室,匾曰‘存恕’,以示及人之意。乡里以疾告,必自为治药,又自视烹之,又自视饮之。曰:‘药虽善矣,烹之不如法,勿验也;饮之不以其时,亦勿验也。疾者之望疗,如望拯溺,故吾不敢以任人。’尝烹药于器,携一童晨往病家,马惊,坠于水,霜天寒甚,起立无愠色,亟索衣易之,上马复往。时已老矣。其急于济人如此。”谢世时,丹溪年33岁,耳濡目染,深受感动。丹溪崇尚医德,可谓一脉相承。
(三)戚氏家学
丹溪母戚氏(1260-1346),为“宋朝奉郎知袁州事如琥之曾孙、从政郎广德军司法参军宋祥之孙、贞孝先生绍之女”,出身诗礼世家,家学渊源。宋濂有《元故朱夫人戚氏墓铭》载其事迹。
外高祖戚如琥,字少白,金华人。从吕东莱游,笃于修身齐家之道以见实用。进士出身,授郴州教授,迁国子博士,出知台州,寻改袁州,政绩大著。门人私谥曰贞白先生。
外从高祖戚如圭,以进士为嵊县尉;戚如玉,亦游太学。宋乾道、淳熙间,兄弟先后连起进士。其母周氏,晚时观书,辄能举大义。尝读《上蔡语录》,顾诸子曰:既不为禄利,复不求人知,斯所谓问学者耶?其期诸子如此。
外曾祖戚宋祥,为宋从政郎广德军司法参军。
外祖父戚绍,入元隐居不仕,同志之士相与号为贞孝先生。
舅父兼岳父戚象祖,字性传。少服家庭之训,弱冠师事王冕(字元章),益达于命义。年几五十,乃用举者得东阳县学教谕,迁绍兴之和靖书院山长。年未七十,辄求致仕,弗许。复用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迄辞不受。和靖、道一书院均为宋、元间江南著名书院,二十年主持这两所书院,也可知其学术地位。后侨居永康之太平。
姑表兄弟、妻弟、同学戚崇僧,字仲咸,贞孝先生绍之孙,象祖之子。年二十,始从白云讲道,同门推为高第。清苦自处,不以时尚改度。每谓人知富贵之可欲,而不知贫贱之可乐也。其父象祖曾访其婿吕汲于永康太平山中,爱之,崇僧遂奉父迁居焉。吕汲之子吕权亦为许谦门徒,而吕汲诸孙则从崇僧学。平素常默坐一室,环书数百卷,非有故不出入。精于篆学,尝以篆法缮写《易》《诗》《书》《礼》《春秋》《孝经》及四书,将献之朝,以《仪礼》一经未及竟,不果上。又尝为书言时政,将诣关陈之,亦不果行。黄晋卿曰:人见君高蹈物表,目以为畸人静者,而不知其未始忘情斯世,第不苟售耳。著有《春秋纂例原旨》、《四书仪对》二卷、《后复古编》一卷、《昭穆图》一卷、《历代指掌图》二卷。
连襟吕汲,象祖婿,事迹不详。其弟吕洙、吕溥,子吕权、吕机均为许谦弟子。
吕溥,字公甫,永康人。从学白云,讲究经旨,为文落落有奇气,诗动荡激烈可喜。冠昏丧祭,一依朱子所定礼行之。所著有《大学疑问》《史论》《竹溪集》。吕洙,字宗鲁,溥之兄。也在白云门,服其精敏,未究而卒。
吕权,字子义,吕汲子,亦从学白云先生。刻苦学习至竟夕不寐,尝自书其梦中之语曰:青壁虽万里,白云只三寻。已而三十八岁病卒。吕机,字审言,吕权弟,亦从白云。通《春秋左氏》,尤精于《资治通鉴》。有笃行。
《格致余论》有案:永康吕亲,形瘦色黑,平生喜酒,多饮不困。年近半百,且有别馆。忽一日大恶寒发战,且自言渴,却不饮。余诊其脉大而弱,唯右关稍实略数,重取则涩。遂作酒热内郁不得外泄由表,热而不虚也。黄芪一物,以干葛汤煎与之。尽黄芪二两,干葛一两,大得汗,次早安矣。这个“吕亲”,似即吕汲。
黄宗羲《宋元学案》有“戚氏家学”专条,戚家五代六人列焉。吕氏二代四人同出许谦门下,与丹溪是亲戚兼同学的关系,并列《宋元学案》的“白云门人”条下。由此亦知,丹溪母家妻族的理学传统和家学渊源,更为深厚。
(四)友人
1.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人,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受业于浙东大儒吴莱、柳贯、黄溍。元末被荐为翰林院编修,推辞不任,隐居乡间著书十余载,一度信奉道教。至正二十年(1360)为朱元璋征召,明开国后历任《元史》修撰总裁官、翰林院学士、国子司业、礼部主事、侍讲学士等职。明代典章制度,“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十三年(1380),因长孙宋慎受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牵累,合家被流放茂州,次年病死于流放途中的夔州(今四川奉节)。正德(1506—1521)中追谥文宪。
宋濂少丹溪二十九岁,自属二代人。宋濂自谓:“盖自加布于首,辄相亲于几杖间,订义质疑,而求古人精神心术之所寓。先生不以濂为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极言而无所隐。故知先生之深者,无逾于濂也。”又说:“予尝从先生游,而交原礼诸父间甚久。”可知宋濂与丹溪过往甚密,交情颇深。
宋濂一生著述丰富,手定《宋学士全集》凡七十五卷,正德间太原张溍刊行;清嘉庆间严荣又合并徐中望、韩叔阳两种刻本,增益为《宋文宪公全集》共五十三卷,另有卷首四卷,为现今通行之足本。集中收有许多与丹溪及其家族、弟子有关的珍贵资料,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题朱彦修遗墨后》《蜀墅塘记》《元故朱夫人戚氏墓铭》《戴仲积墓志铭》《送戴原礼还浦阳序》《赠贾思诚序》《赠医师葛某序》《太初子碣》《义乌王府君墓志铭》《故倪府君墓碣铭》以及《〈格致余论〉题辞》等。由于宋濂与丹溪的密切关系,这些都是可信程度极高的公认的研究丹溪的重要资料。
2.戴良 戴良(1317—1383),字叔能,浦江人,世居九灵山下,自号九灵山人。丹溪高足戴士垚二弟,戴元礼叔父,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少通经史百家、医卜释老之学。与宋濂同出浙东大儒吴莱、柳贯、黄溍门下,二人往来密切。至正间朱元璋初定金华,即命戴与胡翰等十二人会食省中,每日二人更番讲论经史,陈述治道。后又用为学正,与宋濂、叶仪等人培训诸生,但不久即弃官逃逸而去。辛丑年(1361),元顺帝因人推荐,授为江北行省儒学提举,戴良见时事不可为,退避居吴中;见张士诚不足与谋,势将败亡,合家泛海抵山东,居昌乐县数年。洪武六年(1373)始南还,变姓名隐浙东四明山,对明太祖取不合作态度,而与滑寿、项昕、吕复等医学家交厚。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物色得之,召至南京,命居会同馆,将要封官,但戴良借口年老多病固辞不受,因而得罪了朱元璋。次年四月自杀暴卒。
戴良兄士垚、侄元礼、子思温均师事丹溪,为其高足,故戴良亦与丹溪颇多交往。所著《丹溪翁传》是丹溪研究的重要资料。丹溪逝世后,戴氏曾谒丹溪墓并作诗以记:“杨公泣路歧,阮生哭途穷。抚心苟有怀,出涕岂无从?吞声度重阜,衔恨眺连峰。若人久已没,古士将谁逢?时春卉木芳,胜会嘉友同。岂无樽中醑,尽洒坟上松?埋玉惮遗迹,解剑惭古风。长歌欲自慰,情心眷弥重。”
戴良著有《春秋经传考》《和陶诗》和《九灵山房集》等。《九灵山房集》共三十卷,除《丹溪翁传》外,还收有《抱一翁传》《沧洲翁传》《〈脾胃后论〉序》《滑伯仁像赞》等,记载了当时浙江名医的事迹。
3.胡翰 胡翰,字仲申,金华人。从吴师道受经,从吴莱学古文词,又登许谦之门,获闻考亭相传的绪。所以,与丹溪同出许谦门下。元末世时不靖,避地南华山中著书。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初定金陵,即遣使召见;后为衢州府学教授。洪武八年乙卯(1375),明太祖聘修元史,分撰英宗、睿宗本纪及丞相拜住等传。书成,赐金缯。辞归,居长山之阳,学者称长山先生。卒年七十五岁。
胡翰与丹溪为同学兼姻亲,其云:“余辱同门,申之以婚姻。(丹溪)每入城,不以敝庐不足留,留或信宿。士大夫相过,坐席恒满。剧谈古今天下事,至安危休戚之会,慷慨悲凄或泣下数行,意象类齐鲁奇节之士。”二人交情深厚,《赤岸朱氏宗谱》收有胡撰《忆丹溪先生哀辞》,既有丰富的资料可资参考,更见真挚感情溢于言表。
4.叶仪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立志坚苦,取四部书分程读之,义有未明,质于白云许先生。学业日进,以至许谦命其子存仁、存礼师事之。许谦卒后,叶仪率同门治丧毕,即开门授徒,东南之士多趋之。洪武初年,郡守王宗显起为五经师。学者尊为“南阳先生”,所著有《南阳杂稿》。卒年八十二岁。
《古今医案按》载有丹溪治叶仪痢疾危症案,叶仪云:“岁癸酉秋八月,予病滞下,痛作,绝不食饮。既而困惫,不能起床,乃以衽席及荐阙其中而听其自下焉。时朱彦修氏客城中,以友生之好,日过视予,饮予药。但日服而病日增,朋游哗估议之,彦修弗顾也。浃旬病益甚,痰窒咽如絮,呻吟恒昼夜。私自虞,与二子诀,二子哭,道路相传谓予死矣。彦修闻之,曰:此必传者之妄也。翌日天甫明,来视予脉,煮小承气汤饮予。药下咽,觉所苦者自上下,凡一再行,意冷然。越日遂进粥,渐愈。朋游因问彦修治法。答曰:前诊气口脉虚,形虽实而面黄稍白,此由平素与人接言多,言多者中气虚;又其人务竟己事,恒失之饿而伤于饱,伤于饱其流为积,积之久为此证。夫滞下之病,谓宜去其旧而新是图,而我顾投以参、术、陈皮、芍药等补剂十余帖,安得不日以剧?然非此浃旬之补,岂能当此两帖承气哉?故先补完胃气之伤,而后去其积,则一旦霍然矣。”丹溪此案完全参照罗知悌治病僧案,先补后攻,得取全功,是丹溪“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治疗思想的充分体现。此案亦载《格致余论》,文字略有差异。
5.郑太和 宋濂云:“浦阳郑太和十世同居,先生为之喜动颜面。其家所讲冠婚丧祭之礼,每咨于先生而后定。”《浦江县志·流寓》载:“震亨尝至浦之麟溪,为郑氏纂定家范。”其《孝友》载《郑太和传》,云:“至元元年冬,以太常博士柳贯上状复其家,部使者余阙为书‘浙东第一家’褒之。”所以,丹溪与浦江郑家交往极为密切。
《格致余论》《局方发挥》分别载有丹溪治疗其病的二则医案:
义门郑兄年二十余,秋间大发热,口渴,妄言妄见,病似邪鬼。七八日后,召我治,脉之两手洪数而实,视其形肥,面赤带白,却喜露筋。脉本不实,凉药所致。此因劳倦成病,与温补药自安。曰:柴胡七八帖矣。以黄芪附子汤冷与之饮,三帖后困倦鼾睡,微汗而解,脉亦稍软;继以黄芪白术汤,至十日脉渐收敛而小,又与半月而安。
浦江郑兄,年近六十,奉养受用之人也。仲夏久患滞下,而又犯房劳。忽一晚正走厕间,两手舒撒,两眼开而无光,尿自出,汗出雨,喉如拽锯,呼吸甚微,其脉大而无伦次、无部位,可畏之甚。余适在彼,急令煎人参膏,且与灸气海穴。艾炷如小指大,至十八壮,右手能动;又三壮,唇微动;参膏亦成,遂与一盏,至半夜后尽一盏,眼能动;尽二斤,方能言而索食;尽五斤而利止;十斤而安。
(刘时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