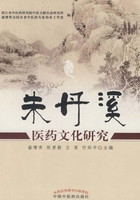
朱丹溪是否养阴派的探讨
丹溪首创滋阴降火,为养阴派的代表医家,似乎已是医界定论。近时,随着对其学术思想研究的深入,人们纷纷提出“丹溪是否养阴派”的疑问。或以为不得以一鳞半爪之言而冠以滋阴大师;或以为作养阴学派的启蒙则可,作代表人物则当商榷;或言其“养阴之法虽立,养阴之方未备”;或言“认丹溪为养阴学派之大师,实失丹溪学说之真谛”,“当以四伤学说为核心”;也有人以为丹溪不是真正的养阴派,而是“泻相火派”。20世纪80年代初,更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从丹溪的理论和医学实践来看,丹溪不是养阴派。当然,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也有调和二种观点的。众说纷纭,而问题的实质是,应如何从总体上评论、认识丹溪的学术思想。在对丹溪主要医学观点和辨证论治心法进行了分析研究之后,本文试就此进行讨论。
(一)对丹溪学术思想评论述要
对丹溪学术思想的评论,早在丹溪逝世之初即在其友人、弟子中展开。明代丹溪学派最为活跃时,评论渐趋深入,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也渐趋激烈。至清代中期,《四库全书》一锤定音,丹溪是养阴派的认识遂成为定论。了解这一评论的发展脉络,对于我们如何从总体上把握丹溪学术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1.丹溪友人的评论 元末明初,丹溪逝世之后不久,友人戴良著《丹溪翁传》,宋濂著《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以纪念丹溪,同时也开研究丹溪之学的先河。
宋濂的《石表辞》着重评论其思想修养、道德作风、政治态度等,但对丹溪医学思想并无多涉及;《宋学士文集》还收有许多与丹溪及其家族、弟子有关的其他资料,但是作为文学家、政治家,他注重的并不是医学思想,对此也并不在行。所以,宋濂的著作没有多少医学思想评论。
大约是少习医卜,兄弟子侄又为丹溪弟子的原因,同为文学家的戴良则着重评论丹溪的医学思想。他说:“翁讲学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为翁墓志,兹故不录,而窃录其医之可传者为翁传,庶使后之君子得以互考焉。”《丹溪翁传》叙述丹溪习医行医、授徒著书的经历,概括《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的主要内容,并记载13则医案以见其医学成就,认为丹溪的学术思想是在“以三家之论去其短而用其长,又复参之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而形成的。这也是丹溪学术思想的由来和总体。“三家之短”在于对“阴虚火动、阴阳两虚、湿热自盛”和“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阐发不够,丹溪故而有二论之作以推广之,亦即补充了《相火论》的内生火热理论和《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谨身节欲的养生论。戴氏并记述了赵良仁问“太极之旨”而悟得丹溪医学的基础在于“阴阳造化之精微与医道相出入”,亦即医学与理学的结合。还记载了一则“翁以阴虚发热而用益阴补血之剂疗之,不三日而愈”的治例,透露了“翁治此犹以芎、归之性辛温而非阴虚者所宜服”的药治方法,大约就是四物汤加黄柏之类。
2.丹溪弟子的评论 丹溪众多的弟子组成强大的丹溪学派,活跃于明代三百年间,把丹溪学术思想传播于全国,并传入日本。丹溪学派的学术特色主要在杂病的气血痰郁火论治,而以滋阴著称者并无所闻。
戴原礼是得丹溪亲传的入室弟子,他对丹溪学术思想的评论主要体现在《金匮钩玄》的按语和后面的六篇论文中,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原礼所补,亦多精确”,“其附以己意,人谓不愧其师”。《金匮钩玄》书后所附的六篇论文中,《火岂君相五志俱有论》和《气属阳动作火论》从“阳有余”的角度论内生火热,把“阳有余”和《相火论》直接联系起来;《血属阴难成易亏论》则从“阴不足”的角度论血之难成易亏,认为“阴气一亏伤”可导致多种多样的血病,把丹溪“阴不足”直接与血病的临床治疗相联系。《金匮钩玄》对痰和六郁的详细论述,更是众所周知。由此看来,戴原礼对丹溪的内生火热和气血痰郁论治的理论和临床都深有心得,这也是原礼对丹溪学说的发展,其基础当然是理解和继承。
赵良仁亦为丹溪入室弟子,所著《金匮方衍义》现可于清代周扬俊《金匮玉函经二注》中见到。其书以《内经》为宗,深得丹溪杂病证治之心传,又能兼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但是书中并未涉及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等观点,也未提及丹溪重视滋阴,或证治中常用滋阴之法等。
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风辨》:“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人异……三子之论,河间主乎火,东垣主乎气,彦修主乎湿”,则以丹溪的学术特点在于“湿”。他对阴阳的看法是,“窃意阴阳之在人,均则宁,偏则病。无过不及之谓均,过与不及之谓偏,盛则过矣,虚则不及矣,其可以盛为和乎”?又说,“人之所藉以生者气也,气者何?阴阳是也。夫阴与阳可以和而平,可以乖而否,善摄与否,吉凶于是乎歧之。夫惟摄之不能以皆善也,故偏寒偏热之病始莫逃于乖否之余”。可见,王履认为阴阳应平衡,有偏则生疾病和有寒热,对丹溪“阳有余阴不足”别有理解。但是书中并未言及丹溪学术特点重在滋阴,或对滋阴情有独钟。
丹溪的另一弟子楼英著《医学纲目》,其《自序》有谓,“仲景详外感于表里阴阳,丹溪独内伤于血气虚实”,并以此为丹溪之所长;所举例论恶热,有气血虚实之热,有表里之热,有真假之热,亦有五脏之热,唯独没有阴虚之热。由此可见,楼英不仅不认为丹溪是滋阴派,他自己对阴虚之证和滋阴之治也不甚了了。
丹溪再传弟子有著作传世者不多。刘纯《医经小学·医之可法为问》通过问答形式,直接以丹溪本人的语调归纳了丹溪的学术思想要点:①医儒一理,读儒书以穷理尽性,格物致知,以知医理;②《内经》为医学之本,仲景、刘、李均有其偏,但古书多缺文讹舛,须着力玩味;③学医须识病机,知变化,不可过求运气;④处方用药须灵活变通;⑤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要义在于,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人其补养残衰伤朽之质,益阴以内守;⑥治病须分血气。其中关于“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说法,有滋阴派的理论雏形:“人之形质,有涯者也,天癸绝后形则衰矣。苟不益阴以内守,则阳亦无以发扬,为健运之能。是天失所依也,而为飘散飞荡如丧家之狗耳。阳既飘散,则地愈失所附也。形气不相依附则死矣。人其补养残衰伤朽之质,又何云哉!”但是,从总体来看刘纯并没有以丹溪为滋阴派的看法。他的主要著作《玉机微义》是在徐彦纯《医学折衷》的基础上增删削补而成的,中心内容多采自刘、张、李、朱四大家以及其他各家之书,也未曾反映丹溪有以补阴为主的特点。
丹溪私淑弟子王纶、汪机、虞抟围绕阳有余阴不足而讨论气血论治的一场学术争鸣,实际上也表明了他们各自对丹溪学说的理解、认识和评论。虞抟医学世家,世代相传尊崇丹溪之学。他对“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解是,“在天地则该乎万物而言,在人身则该乎一体而论,非直指气为阳而血为阴也”,即“阳有余阴不足”并非“气有余血不足”,而是自然界和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现象。因此,他不拘“有余不足”之论而讨论气血阴阳诸虚证及其治法,主张“血虚者须以参芪补之,阳生阴长之理也”,运用于治疗,则主张气虚用四君子汤,血虚用四物汤,阳虚用补气药加乌头、附子之类温阳药,阴虚用四物汤加知母、黄柏或大补阴丸、滋阴大补丸等方药。所以,虞氏并不认为丹溪专擅滋阴,他自己也无滋阴之品的偏颇。
汪机认为丹溪治病“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未尝专主阴虚而治”,“阳有余阴不足论”系指人的生理而非病理。其《营卫论》开宗明义便说,“丹溪论阳有余阴不足,乃据理论人之禀赋也”,目的“无非戒人保守阴气,不可妄损耗也”,“此丹溪所以立论垂于后也,非论治阴阳之病也,若遇有病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未尝专主阴虚而论治”。汪机的医学思想以调补气血为主导,且偏于气的调理,其补气习用参芪,并不擅于滋阴,也不以为丹溪主张滋阴。
王纶《明医杂著》开宗明义即提出对丹溪学术思想的总体评价:“至于丹溪出,而又集儒之大成,发明阴虚发热类乎外感,内伤及湿热相火为病甚多,随症著论,亦不过阐《内经》之要旨,补前贤之未备耳!故曰,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一以贯之,斯医道之大全矣。”而“杂病用丹溪”,丹溪治病不出乎气血痰郁,他说,“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虚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又云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盖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但是,他对《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见解与众不同,《明医杂著·补阴丸论》谓,“人之一身,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况节欲者少,过欲者多。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火旺则阴愈消,而劳瘵、咳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故宜常补其阴,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无病矣。故丹溪先生发明补阴之说,谓专补左尺肾水也。”王氏并立补阴丸方,药用黄柏、知母、龟板、熟地、琐阳、枸杞子、白芍、天冬、五味子、干姜,炼蜜及猪脊髓为丸,亦即大补阴丸中加大量柔润滋阴药。可以说,滋阴学说的理法方药至此初备,这是王氏心得,而非丹溪原意。但王氏并言,这是“丹溪先生发明先圣之旨,以正千载之讹,其功盛哉!”丹溪发明阴虚火旺之说殆即滥觞于此。
3.明代温补学派代表医家的评论 张景岳对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由于张景岳及其著作的巨大影响,丹溪是滋阴派,“阳有余阴不足论”为滋阴降火的病因病机论的观点就广泛传播开来了。
温补派名医,丹溪私淑弟子王纶的学生薛己创真阴真阳之论,其说即附于王氏《明医杂著》而行。他在王氏《补阴丸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设若肾经阴精不足,阳无所化,虚火妄动以致前症者,宜用六味地黄丸补之,使阴旺则阳化;若肾经阳气燥热,阴无以生,虚火内动而致前症者,宜用八味地黄丸补之,使阳旺则阴生”,并引用王冰益火之源壮水之主的两段话作为说明。薛氏的真阴真阳之论和六味丸、八味丸之用,开创了明代温补学派之先河,对其后的张景岳、赵献可、孙一奎等人影响极大,并使王冰“益火之源”“壮水之主”真正成为滋阴温阳两大治则的名言。薛氏没有直接对丹溪学说做出评论,但是其说附于王纶《明医杂著》而行的事实和对《补阴丸论》的发挥,已经清楚表明了他赞同王纶的观点。
汪机的再传弟子孙一奎亦为温补派的名医,他评论丹溪说:“余观近世医家明理学者,宜莫如丹溪。虽倡‘阳有余阴不足’之论,其用意故有所在也。盖以人当承平,酗酒纵欲以竭其精,精竭则火炽,复以刚剂认为温补,故不旋踵血溢内热骨立而毙,与灯膏竭而复加炷者何异。此‘阳有余阴不足’之论所由著也。后学不察,概守其说,一遇虚怯,开手便以滋阴降火为剂,及末期,卒声哑泄泻而死,则曰,‘丹溪之论具在’。不知此不善学丹溪之罪,而于丹溪何尤!”于此可见,阳有余阴不足论当时已成知柏滋阴降火的理论基础,一个“虽”字及后文“阳有余阴不足之谭不可以疵丹溪”,已可见孙氏对“阳有余阴不足”论是颇有微词的,其要点与张景岳相似,也在反对知柏滋阴降火。当然,孙氏态度平和,言词婉转,自不同于张景岳的锋芒毕露,《四库全书》也以为“其说可谓平允矣”。
赵献可在《阳有余阴不足论》的基础上阐述其命门阴阳水火观,强调“自幼至老,补阴之功一日不可缺”,盛赞“自丹溪先生出而立阴虚火动之说,亦发前人所未发”。但是他又感叹“丹溪之书不息,岐黄之泽不彰”,这种矛盾态度的原因在于,赵氏反对“大补阴丸、补阴丸中,俱以黄柏、知母为君”,以致“寒凉之弊又盛行”,强调“火不可以水灭,药不可以寒攻”。
由此看来,温补派医家虽没有直接提出“丹溪是滋阴派”的看法,但颇为一致地认为“阳有余阴不足论”是滋阴降火、立补阴诸丸的理论依据,而当时滥用知柏补阴的风气肇自丹溪。推究其源,盖出自丹溪私淑弟子王纶的《补阴丸论》,经薛己的补充发挥,至孙、张、赵而完成,其间大约经过了一百余年。
4.明清其他医家的评论 明清其他医家对丹溪学说的总体评论大体沿袭王纶的“四大家说”和“滋阴派”说而发挥,以李士材的《医宗必读·四大家论》为代表,时为明末崇祯十年丁丑(1637)。
先是,俞弁著于明嘉靖元年(1522)的《续医说》,并未接受王纶的观点,也没有“四大家”和“滋阴派”的说法。俞氏既认为“丹溪,医之圣者也”,又认为“《格致余论》一书,超迈今古”;但仍不免“窃有可疑者焉”,大体只是枝节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一是“左大顺男右大顺女”之说,独指气血之阴阳,反遗脉位之阴阳,立论有戾经旨;二是醇酒热饮无恙,不宜冷饮;三是士人信行倒仓法,死者相继,且“劳瘵咳血,真阴亏损,脏腑脾胃虚弱,津液枯竭”者,尤为不宜。俞氏评论《局方发挥》说,“丹溪但辩其用药者误耳,非方之罪也,血虚证不宜用香燥之剂,痿痹证不可混作风治,亦何尝屏弃之乎?”也是非常确切的。又借批评赵继宗《儒医精要》评论阳有余阴不足说,“丹溪谆谆勉人养阴以配阳,实非补阴以胜阳也”;而赵氏“驳丹溪专欲补阴以并阳,是谓逆阴阳之常,《经》决无补阴之理”,俞氏以为“继宗何人,而敢轻议如此,多见其不知量也”。字里行间,也可隐约看出他以为阳有余阴不足论是“养阴以配阳”的养生论的看法。
王纶《明医杂著》有四大家之义而未有四大家之名;李士材的《医宗必读》立《四大家论》专篇,其说谓,“仲景张机,守真刘完素,东垣李杲,丹溪朱震亨,其所立言,医林最重,名曰‘四大家’,以其各成一家言,总之阐《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拾,适相发明也。”其评论丹溪曰:“及丹溪出,发明阴虚发热,亦名内伤,而治法又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真水少衰,壮火上亢,以黄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亦阐《内经》之要旨,补东垣之未备而成一家之言者也。”李氏之说为医学界所普遍接受。
清雍正十年(1732)程钟龄著《医学心悟》,以“兼总四家而会通其微意,以各适于用”为著书之大旨;认为仲景、河间长于伤寒、温热、温疫,东垣“卓识千古而于阴虚之内伤尚有缺焉”,故“朱丹溪从而广之,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以补前贤所未及,而医道亦大全矣”。因而,“四子之书,合之则见其全,分之即见其偏”,故须兼总四家而立论。又如乾隆十六年(1751)何梦瑶著《医碥》,谓“河间言暑火,乃与仲景论风寒对讲;丹溪言阴虚,乃与东垣论阳虚对讲,皆以补前人所未备”。虽未直接袭用四大家的说法,意思却是很清楚的。
乾隆五十七年(1792)唐大烈编纂的《吴医汇讲》,是我国最早的医学杂志,其中有关“四大家”的有二文:唐氏自著《张刘李朱后当以薛张吴喻配为八大家论》和徐叶熏《四大家辩》。唐文承李氏之说,谓“久推张、刘、李、朱为四大家者”,以其“各有见地,迭为补阙”,此“已有李士材论之晓畅矣”;他也以为“丹溪又专论补阴,再补东垣之未备”。而徐氏谓,“李士材《读四大家论》一篇,本自王纶大意,谓三子补仲景之未备而与仲景并峙也”,但以为仲景医中神圣,三子不得与之并,其说源自徐灵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徐灵胎著《医学源流论》,其《四大家论》对李士材将张仲景与刘、李、朱并列为四大家大有意见,言辞也就难免过激。他说,“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河间、东垣,乃一偏之学;丹溪不过斟酌诸家之言,而调停去取,以开学者便易之门”,“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见万一,乃跻而与之并称,岂非绝倒”?徐氏之说为后人所接受,四大家遂以张子和取代仲景,大失仲景河间分论外感之寒热,东垣丹溪补内伤之未备的原意。但丹溪是滋阴派已成共识。
5.《四库全书》的评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丹溪学说做了全面评论,《医家类》小序指出,“观戴良和朱震亨传,知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学争也”,并以此为“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标志;其《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提要说,《局方》“盛行于宋元之间,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具有决定医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地位。《四库全书》并以为丹溪与《局方》之争的理论依据是其补阴之说,《石山医案》提要谓,“元朱震亨始矫《局方》之偏,通河间之变,而补阴之说出焉”。其《格致余论》提要归纳丹溪学说为,“其说谓阳易动、阴易亏,独重滋阴降火,创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其《推求师意》提要说,“震亨以补阴为主,世言直补直水者,实由此开其端”。其《金匮钩玄》提要则谓,“震亨以补阴为宗,实开直补真水之先,亦妙阐《内经》之旨,开诸家无穷之悟。虽所用黄柏、知母,不如后人之用六味丸直达本原;所制越鞠丸,亦不如后人之用逍遥散和平无弊。然筚路蓝缕,究以震亨为首庸。”
《四库全书》下了丹溪是滋阴派的定论,并以此作为区分丹溪后学的依据,如《医开》“首载或问数条,谓医学至丹溪而集大成,盖亦主滋阴降火之说者”;又如《志斋医论》“其说云,今之医者多非丹溪而偏门方书盛行,则亦以朱氏为宗者矣”。似乎称誉丹溪,即属以丹溪为宗者,亦即主滋阴降火之说者。此说不妥,其实丹溪弟子的诸多著作,《四库全书》并未言及滋阴降火之说者,如王履《医经溯洄集》、徐用诚《玉机微义》、刘纯《杂病治例》《伤寒治例》、虞抟《医学正传》、方广《丹溪心法附余》等等,并未及滋阴降火。这似乎说明丹溪弟子确实无滋阴一说。
由于《四库全书》具有皇家巨著的极大权威,丹溪是滋阴派,“阳有余阴不足论”为阴虚火旺的病因病机说遂为定论。
先于《四库全书》,亦为清政府组织编印的《医宗金鉴》注“大补阴丸”条谓,“朱震亨云: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宜常养其阴,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斯无病矣。今时之人,过欲者多,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真阴愈竭,孤阳妄行,而劳瘵、潮热、盗汗、骨蒸、咳嗽、咯血、吐血等证悉作。所以世人火旺致此病者,十居八九;火衰成此疾者,百无二三。震亨发明先圣千载未发之旨,其功伟哉!”这段话出自王纶《补阴丸论》,却被移花接木算到丹溪头上。编写《四库全书》时便照样搬来,这大约是《四库全书》以丹溪是滋阴派的开山祖师的由来。
6.丹溪是滋阴派成为定论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丹溪成为滋阴派的历史定论的形成经过:首先是丹溪私淑弟子王纶提出“丹溪先生发明补阴之说”,将丹溪与仲景、河间、东垣并称;其后,薛己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至明末李士材正式倡四大家之说,以“丹溪发明阴虚发热”之治归纳其学术思想,其说为医学界所普遍接受,“丹溪是滋阴派”遂成共识;最后,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谓“其说谓阳易动、阴易亏,独重滋阴降火,创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震亨以补阴为主,世言直补直水者,实由此开其端”,丹溪是滋阴派由此而成定论。
但是,自丹溪逝世至王纶著成《明医杂著》(1358-1502)近150年间,丹溪友人和弟子的基本认识是,丹溪继承刘、张、李三家之学,善治杂病,擅从气血痰郁火立论,为诸医之集大成者,并未以之为滋阴派。
(二)《阳有余阴不足论》是养生论
《阳有余阴不足论》是《格致余论》的重要篇章,丹溪二大名论之一,也是丹溪学术思想的中心内容。
丹溪这一名论是一养生专论,讨论了人身阳有余阴不足的生理状态,阐发情欲伤阴的机理,进而提出一系列慎身养性的方法,充实和完善了戒色欲的养生理论。
养生在丹溪学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格致余论》卷首便是饮食、色欲二箴,《茹淡论》《房中补益论》《大病不守禁忌论》则进一步具体阐明色食两方面的养生观,《慈幼论》《养老论》则针对不同年龄特点而立论。这些论文与《阳有余阴不足论》两相印证,构成丹溪养生论全貌。
1.阴阳的含义及其有余不足 文中阴阳含义有二:“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以气血为阴阳;其二与生殖机能有关,男子十六精成,女子十四经行,“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慈幼论》说,“人生十六岁以前,血气俱盛……唯阴长不足”,阴不是气血而是生殖机能的物质基础。与此对应的“阳”,丹溪未曾明言其意义及正常状态,所论都属有余的情欲过极,相火妄动的异常现象。朱熹有言,“神知,阳之为也……阳主辟,凡发畅宣散者,皆阳为之也”,丹溪结合河间“五志皆能化火”的观点,认为精神情志活动都属“阳动”,强调“凡动皆属火”。论中以情欲之动可触发君相火动,故“阳”特指无涯的情欲亦即追求性满足的欲望而言。气血是成精孕胎的基础和源泉,论气血是为论精血情欲铺路,全论以戒色欲为宗旨,这里的阴阳含义就同一般的理解大异。
因此,阳有余阴不足的实质就是“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为讨论这种不平衡的关系,丹溪用了四方面的论据:一以天地日月为喻;二言阴气难成易亏的生理特点;三论情欲无涯的一般倾向;四是引经据典,用《内经》的旨意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二、三两点。
阴气难成,难在必待男十六女十四才精成经通,具有生育能力,“以能成人而为人父母”;易亏,“四十阴气自半”,男六十四,女四十九,便精绝经断,丧失生育能力。所以,“阴气之成,止供给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这是时间上相对的“阴不足”。
一般人过分追求情欲的倾向,更促进了这种“阳有余阴不足”的不平衡关系。《色欲箴》指出,“眴彼眛者,徇情纵欲,唯恐不及”,阳既太过,阴必重伤,精血难继,于身有损,“血气几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为我贼”。这是从“量”的对比上理解“阴不足”。丹溪感叹,“中古以下,世风日偷,资禀日薄”的社会风气,强调无涯情欲的“阳”与难成易亏的生殖物质的“阴”,存在着这种难以摆平的“供求”关系。孙一奎所谓承平之世,“人多酗酒纵欲,精竭火炽”,丹溪出而“创此救时之说”,这正说明了丹溪提出养生理论和方法的现实要求和社会需要。
以天地日月说明人身阴阳气血的有余不足,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逻辑学上叫类比。但是,类比不能提供必然正确的结论,其结果还有待于证明。同样的天地日月,张景岳由此得出“阳非有余”的结论。故《四库全书》批评二人取譬固是,却“各明一义而忘其各执一偏,其病亦相等也”,实质上指出了类比的局限。所以,丹溪这种推理得出的结论,主要还是由阴易亏阳易动的实践观察资料证明的。由于天大地小日实月缺是正常的自然现象,类比的结果也只能是生理现象,丹溪不以同样的类比说明“相火妄动,煎熬真阴”的病变,也可作为佐证。古人也认识到这点,丹溪后学刘纯也曾提出,“阴阳虚实之体既不同,而升降之用,所乘之机,既无降杀,则阴之体本虚,曷用补哉”的问题。
为加强论据,丹溪又援引《内经》为证,但这是令人遗憾的败笔,反削弱了原文的论证力量。《太阴阳明论》“阳道实阴道虚”,意即外感多实内伤多虚;《方盛衰论》“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阴阳指天地之气,为假设之辞,以证天地阴阳之气交互升降之理。阴阳含义不同,并不能得出“观虚与盛之所在,非吾之过论”的结论。故张景岳批评丹溪“引此虚实二字以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其说左矣”,确实切中要害。丹溪引证经旨,反致授人以柄,多一批评口实,亦是智者千虑之失。其实,以阴阳论人身精血与情欲关系,本是旷古未闻的独创见解,可谓之前无古人,哪里引得到现成的经典意旨或名人大论呢?
2.情欲伤阴的机理和养生措施 丹溪认为生殖物质之“阴”由肝肾所控制,“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职责又有分工,其中枢纽却是相火。“相火静而藏则属肾,动而发则属肝胆”,相火安居,守位禀命,则肾主闭藏,阴得保养;若相火浮动,下牵肝肾,则肝司疏泄,精走阴伤。因此,相火是伤阴过程中的关键。
然而,相火“其系上属于心”,受心的控制和指挥。心为外界事物(本论特指女色)所触,则“易动”而萌生情欲,触发相火,致精走阴伤。丹溪担心人们还不理解他的苦心,更进一步说明,“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强调欲之动,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会丧精伤阴。这一过程可用简单的图式来说明:

这个图式中,从“心动”到“阴伤”是理之自然,因而丹溪着眼于切断这条致病环链的前两个环节,主张“心不妄动”,“不见所欲”,中心是个“心”字,要点在于“静”。
心不妄动主要是个道德修养问题。“圣人只是教人收心、养心,其旨深矣”,《相火论》又一再引程朱的话,念念不忘“人心听命于道心”,劝诫人们以理智控制感情,静心澄志,不要妄为非非之想,以致心动相火起。《房中补益论》进一步指出医儒收心、正心、恬淡虚无的共同目的,都在防止心君火动而引动相火。所以,“静”“心”便成为丹溪谨身节欲的养生观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宗旨相结合的交叉点,孜孜于修身养性的儒理,总还以抑火保精的医学目的为重。
老子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丹溪引以说明,避免心为外物所感,消除触发情欲的外来因素。他说,“夫以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所以,为避免女色的诱惑,或“出居于外”,或“暂远帷幕”。
因此,丹溪收心远色的养生措施,不是“亡羊补牢”,也不是“防微杜渐”,他不仅劝人莫为“非分之事”,更谆谆告诫勿作“非非之想”。整个养生观,围绕一个“心”字,突出一个“静”字,深受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从“存天理灭人欲”观点出发,认为坤道成女,乾道成男,男女配合,毕竟还是“天理”,不可尽革。故主张“必近三十二十而后嫁娶”,“成之以礼,接之以时”,提出“谨四虚”的观点。
所谓“谨四虚”,本诸《灵枢·岁露》“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邪风所伤,是为三虚”之说,又直接接受了孙思邈《千金方·房中补益论》的有关说法。其一为“年之虚”,冬夏四、五、六、十、十一诸月,或火土之旺,或火气之伏,为保金水二脏,“此五个月出居于外”,须独宿而淡味,兢兢业业于爱护;其二为“月之虚”,遵《内经》血气虚实随月之圆缺而变之说,以为须谨上弦前、下弦后,月廓空虚之时;其三为“日之虚”,即气候突变情绪波动之时;又有“病患之虚”,如病患初退,疮痍正作之类,便谨不可犯。所以,“善摄生者”逢年之虚则出居于外,“苟值一月之虚,亦宜暂远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期无负敬身之教”。至于“日之虚”“病患之虚”,他未明言,然其意尽在不言之中,自不难逆料。
丹溪养生论独特与高明之处,在于他通过相火这一中间环节,从理论上阐述了情欲伤阴的机理,并与理学的个人修养和封建道德说教相结合,形成其另一个鲜明特色。这比丹溪前人只作劝戒,立典范,教人如何做而不言所以然来,更加深入,有说服力。
另须一提的是,这篇养生论的适用对象仅是男子。无论是相火伤阴的机理,还是收心养性,敛神涩精的方法,都是针对男子立论的。他认为,“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乐于与,一乐于取,此自然之理也”。故男子耽于色欲则废家丧德瘁身,女子则不过亏闺门之肃,损门庭之和,结果不一,故戴良称此论“远取诸天地日月,近取诸男子之身”。
3.后世评论举要 丹溪此论一出,颇为医界所重,然而后人见仁见智,各自理解不同,认识不一。大体上讲有二类见解,一是以为养生论,气血阴阳的有余不足属生理现象;一是以为病因病机论,阴阳的有余不足是病理状况下的基本机理,从而成为丹溪滋阴论的理论基础。
(1)以为养生论的评论:戴良的《丹溪翁传》可称是最早的丹溪学术评论,其归纳《阳有余阴不足论》为二个问题,一是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何为其然也”?二是“今欲顺阴阳之理而为摄养之法,如之何则可”?一论“阴阳之理”,一论“摄养之法”,前者是后者前提,后者是前者合乎逻辑的结果。评论虽简略,丹溪养生真谛戴氏还是明白的。
明代李梴《医学入门》首卷有“保养”一门,选录《上古天真论》、丹溪《茹淡论》《阴有余阳不足论》(增补内容改题为《阴火论》),自撰《保养论》。文前小序言,“录《天真论》于前者,保养之源也;录《茹淡》《阴火论》于中者,保养不过节食与色而已;更为说于后者,黜邪崇正法赜之贞也”。李氏并有“火不妄动,动出于心,静之一字,其心中之水乎”,“神静则心火自降,欲断则肾水自升”,“主于理则人欲消亡而心神静,不求静而自静”等语,可谓深得丹溪之秘。
汪机《营卫论》开宗明义便说:“丹溪论阳有余阴不足,乃据理论人之禀赋也”,目的“无非戒人保守阴气,不可妄损耗也”,“此丹溪所以立论垂于后也,非论治阴阳之病也”。可见汪氏是视此为养生之论的。汪氏医学思想是重视气血,以气血论治见长,故笔锋一转,“若遇有病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随后便气阳、血阴,卫阳、营阴,把阳有余阴不足纳入其津津乐道的气血论治中去了。考究他这种矛盾态度的缘由,主要还是认阴阳二字的含义不真,以气血为阴阳所致。他认为丹溪所论的禀赋就是气有余血不足,所以举阴不足的例,便取女子经来经断,而舍男子精通精绝;伤阴的例,便取《内经》五劳所伤,误认为保守阴气就是补血养血,可见他是围绕气血来认识阴阳。对养生论的理解本身就不够确切,所以为调和阳气可补的主张同阳有余说的矛盾,费尽心机地兜圈子,也还是捉襟见肘,难圆其说。汪氏若真正弄懂丹溪原意,就可以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见解,根本不必这么转弯抹角。
除汪机外,戴原礼、虞抟也是从气血观点去理解的,且留待下文讨论。
(2)以为病机论的评论:王纶的见解与众不同,他说:“人之一身,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况节欲者少,过欲者多。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火旺则阴愈消,而劳瘵、咳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变丹溪“相火妄动,煎熬真阴”为“精血既亏,相火必旺”,倒因为果,“阳有余阴不足论”遂一变而为病因病机论。进而王纶又说,“故宜常补其阴,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无病矣。故丹溪先生发明补阴之说,谓专补左尺肾水也。”后世所谓丹溪发明阴虚火旺之说即滥觞于此。然而,所谓“精血既亏,相火必旺”,并非《阳有余阴不足论》中应有之义,视为王氏心得则可,以为丹溪原意则否。
张景岳对《阳有余阴不足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景岳全书·传忠录》有专文《辨丹溪》九条,又有《阳不足再辨》,未尽之意又有《质疑录》的《论阳常有余》《论气有余即是火》等篇之作。反复论辩的要点只是一个,阳非有余而真阴不足。但是,景岳的论证方法似乎并不合乎逻辑:他只是一再反复强调真阳之气的重要意义,批评丹溪立论不当,引证“阳道实、阴道虚”等不合经意,天地日月的类比有不同的结论,尤其强烈反对以知母、黄柏泻火补阴的方法,却从未分析丹溪此论的“阴”“阳”二字的切实含义。这一“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使张氏的雄辩成了无的放矢,失去了意义。但是,由于张景岳及其著作的巨大影响,“阳有余阴不足论”为滋阴降火的病因病机论的观点就广泛传播开来了。
汪机的再传弟子孙一奎则以貌似不偏不倚的态度来调和两种观点的矛盾:“盖以人当承平,酗酒纵欲,以竭其精,精竭则火炽,复以刚剂认为温补,故不旋踵血溢内热骨立而毙,与灯膏竭而复加炷者何异?此阳有余阴不足之论所由著也”。从劝诫人们不得纵欲竭精的写作目的而言,孙氏是认识到丹溪养生论的性质的;他又以为“精竭则火炽”,也颠倒了原论“火动而精走”,倒因为果,则又赞同王纶的病机论;但又批评了以此为滋阴降火论而致滥用苦寒清降之剂的谬误:“后学不察,概守其说,一遇虚怯,开手便以滋阴降火为剂,及末期,卒声哑泄泻以死,则曰丹溪之论具在。不知此不善学丹溪之罪,而于丹溪何尤”?四平八稳的说法中隐含着赞同病机论的基本态度,且言词婉转,很得《四库全书》的赞赏,谓“其说可谓平允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说谓阳易动、阴易亏,独重滋阴降火,创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张介宾等攻之不遗余力。然震亨意主补益,故谆谆以饮食、色欲为箴。所立补阴诸丸,亦多奇效”,“阳有余阴不足论”遂成为重滋阴降火、立补阴诸丸的理论依据。作为提要,这个论点没有也不必论证,且兼及“谆谆以饮食、色欲为箴”的养生观和孙一奎“创此救时之说”的写作动机,对朱、张二家的论争又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公允态度,更加以皇家巨著的极大权威,“阳有余阴不足论”的病因病机说遂为定论。
(三)《相火论》是内生火热论
丹溪在《内经》“少火壮火”说的基础上,继承了河间火热论、东垣阴火说,并吸取陈无择、张子和若干观点,提出了相火的生理病理理论。《相火论》创造性地发展了内生火热理论,使祖国医学对火热病证的病因病机,辨治规律认识都有了长足进步。这是丹溪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丹溪对医学的重大贡献。
1.君火、相火的两套概念 《素问》君火、相火言运气,丹溪借用这两个名词,而赋予生理病理情况下的不同概念。这是《相火论》的中心内容。
丹溪以为,五行之中,火与其他四行不同,五行“各一其性,唯火有二”。二火的共性是“动”—“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君、相二火的区别则在,“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即由于名位之异,形气之别,五行归属不同而分君相。君火即指有形、有气、有名,五行属火的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更特指精神情志活动。相火无一定形质,不独居一脏,因其活动而有所表现,特指人身生生不息的功能活动的动力。丹溪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天主生物”是比喻,人能恒于动则是相火的功能表现,所以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以此说明相火的生理意义,所以相火概念的外延比起君火来要广得多。《阴有余阳不足论》的相火属生殖功能活动,归于肝肾,上属于心,心动则火起精走即是相火生理的具体一例。
病理性君相火则全然不同,“君火之气,经以暑与湿言之;相火之气,经以火言之,盖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暑湿俱为六淫,君火当属外感火热;相火因“五性感物”而动,证分脏腑而言,当为内生火热。君相之别在外感、内生之异。
此外,还有相火为天火、龙雷之火,君火为人火之说,其实质意义不大。
2.相火病因病理 《相火论》的中心内容是阐述相火,亦即内生火热的病因病理。丹溪强调二个关系,一是君相火关系,一是相火和阴的关系。
君相火关系的实质是精神情志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主要内容是相火病因意义,上文已详。丹溪引用周敦颐的“神发知矣,五性感物而善恶分,万事出矣”,说明人于有知之后就有“为物所感不能不动”的本性,而“动”即为五火,由是触发相火而导致一系列病变。这一病因说,很明显是刘河间“五志化火”说的移植。
相火与阴的关系,生理状况下相火有赖于阴,病理状况下则相火伤阴。丹溪以天火本于地比喻其生理关系,言雷非伏不鸣,龙非蛰不飞,海非附于地不波,鸣、飞、波虽属动而为火者,力量来源却在蛰伏附地的过程中取得。以此类比,“肝肾之阴悉具相火”,说明人身功能活动的动力有赖于脏腑组织的生命物质。病理情况下,“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因而“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气之贼”。其说本于《内经》“阳胜则阴病”“壮火食气”之旨,申明内生火热的病机特点,进而丹溪以病机十九条的五条火证为纲,脏腑病状为目,又引《原病式》脏腑诸火之动、升、胜、用,讨论相火表现,“出于脏腑者然也”。以脏腑辨证为内生火热的主要辩证方法是《相火论》的重要内容,联系《格致余论》自序“湿热相火为病甚多”,这种相火当非阴虚生内热之虚火,亦非气虚下陷之火,“气有余便是火”,偏指机体脏脏阴阳平衡失调所致的内生实火。
近时,人们普遍注意到丹溪相火生理说明对明代命门相火说的影响,指出二者一致之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丹溪相火生理说的不足之处,即只是局限于一种抽象的概念和空泛的推理,除了人“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等笼统的话语外,就是天地龙雷之类玄妙怪诞的比喻,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和具体内容。其实,《相火论》的主旨在于阐发其病理,故从病因病机到症候表现,辨证观点,无不一一言明,连防止相火妄动之法也考虑到了。两相比较,这种生理说只不过是一种陪衬,全文的重点和中心内容全在相火病理之变上;这正如《内经》论六气之常变,归根到底在于六淫之变的病理意义。陈无择的君火论与丹溪的相火生理说毫无二致,只是不言病理,故丹溪批评他“不曾深及”。
(四)丹溪与养阴理论
人身之阴有三,肺胃之阴为津液,心脾之阴是营血,肝肾之阴即精髓。所谓丹溪“发明阴虚火动,开直补真水之先”,则是从肝肾之阴着眼;而后世一般所称的阴虚和滋阴学说,也都是就肝肾阴精而言的。阴虚证的基本病机特点是阴虚不能制阳机体内部阴阳失调而见一系列的虚热病象;其治则紧紧抓住肝肾之阴这个关键,滋阴火自降,壮水阳方敛。这个病机和治则是滋阴理论的中心环节。
1.丹溪与阴虚阳亢的病机理论 以“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和术语讨论病机,丹溪之前早就频繁广泛地运用了。《内经》以此言邪正,有余之阳为邪气,不足之阴为精血,“阴气不足则内热,阳气有余则外热”,“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其病机可虚可实,既有内伤,亦有外感,其病则有风水、肉烁、瘅疟等。《诸病源候论》以此解释机体内部阴阳平衡失调,而偏重于内伤杂病范围,明言“非邪气从外来乘也”,其病因出于血气之虚,基本病机是虚劳而热,可见烦闷、上气、身热、唇口干、小便赤等症象。刘河间倡言“水善火恶”,以为“水虚则热”,反对用热药补肾水以退心火的观点。河间的阴阳特指心肾二脏,中心问题则是主张火热论。李东垣的学术观点素重脾胃,重阳气,但在论及“饮酒过伤”时,则以“阴不足阳有余”论其伤元气的机理:酒性大热,易伤元气;若以大黄之属下之则“亦损肾水,真阴及有形阴血俱为不足,如此则阴血愈虚,真水愈弱,阳毒之热大旺,反增其阴火,是以元气消耗,折人长命,不然则虚损之病成矣”。真阴属肾,与有形阴血不同,虚则热旺增火而成虚损。可见东垣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对以肾阴为中心的阴虚火旺病机已有一定认识。概括而言,丹溪以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是不断发展的病因病机观,总的趋势是从大范围的笼统内容到特定含义的明确概念,从邪正对立到机体内部阴阳失调,从“阴不足”“阳有余”相并立到“阴不足”导致“阳有余”的因果关系,认识在不断演变、深化,逐渐接近后世的阴虚火旺病机认识。
如同上文所讨论的,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一反前人的病因病机观点,其阴指生殖物质,阳指情欲,中心环节是生理情况下的养生,并未论及阴虚火旺的病机。王纶所谓“精血既亏,相火必旺”,指为王氏心得则可,视为丹溪原意则否。《相火论》专论内生火热,以七情解释病因,用五脏进行辨证,这一相火属“气有余便是火”,偏指机体脏腑阴阳平衡失调所致的内生实火。虽能“煎熬真阴”,导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的病理结局,但这只是“阳胜则阴病”,与阴虚导致阳亢的阴虚火旺病机,正有虚实之别,自然不可混淆。因此,丹溪两大名论实与阴虚阳亢的病机理论无关。
丹溪《格致余论》曾散在地以阴虚阳亢的病因病机观论及许多疾病和症状。河间曾言“老人之气衰”则为“阴虚阳实之热证”,丹溪本此而论衰老是“阴不足以配阳,孤阳几欲飞越”,因此,“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后,精血俱耗,平居无事,已有热证”,常常表现为“头昏目眵,肌痒溺数,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聩,健忘眩晕,肠燥面垢,发脱眼花,久坐兀睡,未风先寒,食则易饥,笑则有泪”的老态,虽然这一系列证象只属“但是老境,无不有此”的生理现象,其机理的认识则与阴虚阳亢病机接近了一大步。《格致余论·恶寒非寒病恶热非热病论》引《内经》“阴虚则发热”,阳在外阴之卫,阴在内阳之守之理论,认为恶热是“精神外驰,嗜欲无节,阴气耗散,阳无所附,遂致浮散于肌表之间而恶热也,实非有热,当作阴虚治之而用补养之法可也”。主要在于就恶热这一证候鉴别病证虚实,意在阐发内外伤之辨,立足点在东垣的气虚发热观点。这些说法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阴虚火亢病机,但远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而且就其深度和广度言,也未出其先辈刘、李诸人之上。因此,以为丹溪对阴虚火亢病机有深刻认识,甚或“发明”此说,根据似嫌不足。
真正完善阴虚阳亢病机理论的当为明代温补学派。张景岳以形质言“真阴之象”,以命门为“真阴之脏”,以“皆不足”论“真阴之病”,以益火壮水论“真阴之治”,并创立左右归丸、饮,理法方药一以贯之,形成了系统的完备理论。而景岳此论的写作目的,竟然是为了澄清刘、朱之说,“使刘朱之言不息,岐黄之泽不彰,是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其根本原因在于,丹溪《相火论》从“相火暴悍酷烈煎熬真阴”的角度立论,病机中心是“阳胜则阴病”,是实火伤阴;而景岳的“真阴论”着眼于阴病皆不足,从阴虚火动立论,病机中心在肾命真阴之虚,阴虚不能制阳,以致虚阳上亢而见虚热病象。二者虚实相反,学术见解正如冰炭之异。所以,景岳将河间丹溪相提并论,取激烈的批判态度,是学术见解的对立所致,并非出于成见,意气用事。这也从反面证明,丹溪对阴虚火旺的病机缺乏深入认识,更谈不上创立滋阴学说,启迪养阴学派的形成。
2.丹溪与滋阴降火的治则理论 《内经》“虚则补之”的治则针对所有虚证而言,包括了滋阴理论在内,“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已示大法,但指导临床尚缺乏针对性和具体内容。王冰注《内经》“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曾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名言,原意本是“脏腑之源有寒热温凉之主”,即水火二脏分主寒热,补心可除寒,壮肾能制热,后人借作滋阴壮阳两大治则,在医学史上留下重要影响。宋代钱乙化裁金匮肾气丸为六味地黄丸,后世称为“直补真水之圣药”,根据便在“肝藏相火,易动而当泻;肾寄真水,易亏而当补”。可见滋阴治则早在丹溪之前就已有一定发展,方药也初具规模。
丹溪的养阴保阴观点有三:一是《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观点,主张静心澄神节欲养性,使相火守位而不妄动伤阴,这是未病先防的养生观而非治则;二是《相火论》的观点,主张清泻妄动之火使不伤阴,泻相火求保阴,实则泻之,既病防变,属泻实治则而非补虚;三是“有补阴即火自降者,炒黄柏、地黄之类”,“阴虚发热用四物汤加黄柏……是补阴降火之妙药”,这散见于《金匮钩玄》诸多病证的治则治法中,也是丹溪有关论述中最接近于滋阴降火治则的表述,须加认真分析。丹溪未曾明确阐述“阴”的含义,指出其症候,故难以直接判别其性质。丹溪常指血为阴,四物汤是补血主方,以为熟地“大补,血衰者须用之”,所以这里的“补阴”实际上指的是补血。《金匮钩玄》后附《血属阴难成易亏论》,引证《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观点以论阴血难成易亏的生理和多种血病病证,讨论四物汤的药物组成和临证运用,是补血主方,并明确指出“此特论血病而求血药之属是也”。所以补阴即补血更符合丹溪的整体思想。明代温补学派的著名医家赵献可就一再批评丹溪“阴字认不真,误以血为阴耳”,用四物汤是“以润血为主而不探乎肾中先天之源”;这一批评也是切中要害的。赵氏主张“滋其阴则火自降,当串讲,不必降火也”,以六味丸补水配火,治“肾虚不能制火”,“阴中水干而火炎上者”。赵氏围绕“肾中真阴”来讨论证治方药,与张景岳的真阴之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才是真正确立了滋阴降火治则,形成完整的滋阴学说。
因此,无论是病机还是治则,丹溪在滋阴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缺乏大的建树;而滋阴理论在丹溪的学术思想中也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一事实支持“丹溪不是养阴派”的说法。
(五)丹溪证治方药分析
证治方药能从医疗实践角度说明丹溪与养阴学说的关系,是证明“丹溪是否养阴派”的重要依据,试与简要分析。
1.丹溪证治分析 丹溪证治与理论相一致,能反映其气血痰郁火的病机认识,也能反映其注重保护正气的治疗观点,但支持滋阴降火观点则不充分。
《格致余论》论病机,或言血气之虚,或责痰火之盛。《金匮钩玄》139门,称阴虚的有10门。其言“劳瘵主乎阴虚,痰与血病”,劳瘵的常见症状,如“午后嗽多者,此属阴虚”,喘“有阴虚,小腹下火起而上者”,盗汗亦“阴虚”,发热“阴虚难治”,治疗基本方是四物汤,所加或人尿、姜汁,或知母、黄柏,或龟板、黄柏,或枳实、半夏等,其意正与前述“补阴火自降”的“阴”同。总的意思还如赵献可所言“以血虚作阴虚”,故劳瘵的主症咳血、咯血,又责之血虚而用四物汤。此外,耳聋门“有阴虚火动耳聋者”,则“须用四物汤降火”,这个阴虚的性质与劳瘵诸证相类似。注夏门“属阴虚,元气不足”,症见头痛脚软,食少体热,治用补中益气汤去升麻、柴胡,加炒黄柏,实为气虚发热证。脚气门“大病虚脱,本是阴虚”,主以人参,且须“多服”,并以艾灸丹田;大体与前治“浦江郑义士”案同,明属阳脱。噤口痢门“热不止者属阴虚,用寒凉药,兼升药”,这个“阴”性质难定。所以,《金匮钩玄》全书称阴虚的10门中,只有劳瘵诸证一组五门有明确的阴虚性质,但丹溪又混同血虚为治,其余则非阴虚证。
但是,许多一般情况下常属阴虚的病证丹溪却不这样认识。例如中风病,河间责之“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已很明确地从阴虚阳亢的角度认识其基本病机;丹溪却以气虚、血虚、湿痰立论,而不同样地认为阴虚火动生风。丹溪之学上承河间余绪,对河间的火热论颇多发挥,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完全抛开了师门的见解,只能证明一点:丹溪并不习惯于从阴虚阳亢的角度论病,更谈不上创建滋阴学说了。眩晕,丹溪有“无痰则不能作眩”的名言,与河间的“风火兼化而主动”,景岳的“无虚不能作眩”,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病机认识,各具特色,反映了各自的学术本旨,当然非出偶然。
与证治认识相一致,丹溪的医案也多以气血痰郁火进行辨证论治,现存医案仅有5例责之阴虚的,且未见现今所通认的阴虚症状,也未运用滋阴之品。由此看来,丹溪的医疗实践并未从阴虚阳亢角度认病识证,也并未以滋补阴精为治疗大法。故多种主张丹溪为滋阴学派代表医家的著作,如《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竟然无法举出一则滋阴医案作为其医疗实践的根据,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2.丹溪方药讨论 丹溪方药与“是否养阴派”问题有关的,主要是知母、黄柏二药和补阴诸丸。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的:“丹溪以补阴为宗,实开直补真水之先……虽所用黄柏、知母,不如后人之用六味丸直达本源”;又说,“所立补阴诸丸,亦多奇效”。本节试就此进行讨论。
(1)知母、黄柏:《本草衍义补遗》载,知母,“阴中微阳,肾经之本药,主消渴热中,下水,补不足,益气,骨热劳,传尸疰病,产后蓐劳,消痰止嗽,虚人口干用而用之”,末句“用而用之”句意不明;黄柏,“蘖皮属金而有水与火,走乎厥阴而有泻火而为补阴之功。配细辛治口疮有奇功”。
丹溪之前,洁古、东垣都有知柏滋阴之说。张洁古《医学启源》谓黄柏“能泻膀胱龙火,补肾水不足,壮骨髓”,知母“补益肾水”;李东垣则以知柏配肉桂为滋肾丸。丹溪却从其《相火论》的内生火热观点出发以为“泻火而为补阴之功”,着眼于泻火。这一点在丹溪的证治中得到切实反映。《金匮钩玄》全书139门中,20门34方用黄柏,其中4门知柏同用。其用法有三:12门23方用于清泻实热相火,7门8方在补益药基础上配合运用以扶正祛邪,3门3方专清血热,三种用法的目的均在泻火,即《相火论》“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泻水中之火是也”,泻火而间接保养阴气,并非直接用作滋阴要药。故匡氏据此称其为“泻相火派”,确也不无道理。若从实践角度言,丹溪医案344则中,用黄柏54案,位居用药频度之14,用知母17案,更远远居后于第41位,比附子的第36位还落后。
由此可见,《四库全书》以为丹溪用知柏滋阴“直补真水”,并不合丹溪原意;而张景岳指摘丹溪滥用知柏苦寒滋阴,实属误解。不过,明代中后期医学界确实有滥用知柏滋阴的风气,因而绮石论治虚劳,有论辩禁用黄柏、知母滋阴的专文;李时珍也有相似的看法;也难怪张景岳有偏激的反对态度了。但是,其始作俑者确实不是朱丹溪。
(2)补阴诸丸:补阴诸丸即三补丸、大补丸、大补阴丸,出《丹溪心法》。三补丸用黄芩、黄连、黄柏三药,功能“治上焦积热,泻五脏火”;大补丸用单味黄柏水丸,“去肾经火,燥下焦湿”;大补阴丸《心法》原名亦为大补丸,用知母、黄柏、熟地、龟板为末,以猪脊髓蜜丸,“降阴火,补肾水”。前二方纯用大苦大寒以泻火燥湿,后者兼用滋阴之品而有补阴降火之功。
《金匮钩玄》呃逆门言“有痰、气虚、阴火,视其有余不足治之”,“不足者人参白术汤下大补丸”,这大补丸应是单味黄柏。《格致余论》责呃逆属火,主张补虚降火,所援二案均用人参白术汤,一下益元散,一下大补丸,故此处大补丸枉有大补之名而纯属泻火之品。《古今医案按》《宋元明清名医类案》引用此方时不言大补,径作“以黄柏炒燥研末,陈米饭丸”。《丹溪心法·补损》则谓大补丸“气虚以补气药下,血虚以补血药下,并不单用”,可见大补丸不能独立运用,当然难能视为丹溪补阴代表方了。
《金匮钩玄》腰痛门、痿门载有补阴丸,但有方无药;虞抟谓是虎潜丸,方用知母、黄柏、熟地、龟板、白芍、陈皮、牛膝、虎胫骨、琐阳、当归,颇多滋阴之品而有补肾强腰之功。但与大补阴丸自是不同。
此外,三补丸、大补阴丸无论丹溪著作还是医案均无所见;《丹溪心法》程充在诸方后加按语谓:“诸补阴药,兼见于各症之下。杨氏类集于此,又取燥热兴阳诸方混于其间……欲并去之,而用者既久,今明白疏出,俾观者知其旨而自采择焉”,则知诸方出于丹溪证治而经杨殉类集,后人运用既广且久。但是从出处看,丹溪本人却无多运用,说是丹溪滋阴降火的代表方,难以令人信服。若三补丸纯用大苦大寒,组成类似黄连解毒汤,无论是否出自丹溪之手,都不能说是补阴方。
(3)用药规律:上文曾统计了丹溪医案344则中319则有方药案的用药频度,医案用药频度最高的药物是补气养血药;其次是清热化湿祛痰药;再次是理气散郁行滞药;而常用的滋阴药并不多用。这一用药规律正确地反映了丹溪杂病辨治注重气血痰郁火的思想,而看不出一个养阴派的用药特点。有人统计了30余首常用养阴方剂,所用药物以地黄、麦冬居首,其次是阿胶、龟板、元参、白芍,再次是石斛、知母、玉竹、枸杞子、黄精等,其他如山萸肉、酸枣仁、沙参、百合等。这些药物中,除地黄、白芍外,其余诸药丹溪都很少运用,两相对照,亦足以说明丹溪临床实践并不像一个养阴派。
因此,无论证治观点还是方药运用,丹溪的医疗实践并没有特别注重养阴,甚至并没有多少养阴的内容。这一事实也支持“丹溪不是养阴派”的说法。
(六)丹溪成为养阴派的原因初探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医学学说的倡导者,医学派别的代表人物,应当具有鲜明的特点:其医学理论应当大大地充实、丰富和完善前人的学说,自成体系,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其医学实践必然广泛地运用这种理论去认病识证,辨证论治,自订新方或利用前人成方来实现这一观点;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必然会充分反映在他的医案里。丹溪之前的河间火热论,东垣脾胃论,子和攻邪说,丹溪之后孙一奎、张景岳、赵献可的命门说,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的温病学等等,无不如此。然而,丹溪的病机认识、治则治法、辨证规律、方药运用,从理论到实践都缺乏作为养阴派的倡导者或代表医家的特点,他的学生评论其学术要点也只是说“杂病用丹溪”,“治病不出气血痰,三者又每兼郁”,“集诸医之大成”等等,并未言及滋阴派之一字。因此,认为丹溪不是养阴派的看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能令人信服的。
但是,“丹溪是滋阴派”已成历史定论,数百年来人们一直以讹传讹,自有一定原因。笔者据手头有限资料,归纳其因为“四个误解,一个需求”,试作初步探索。
首先是对《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误解。由于阴阳概念欠清,遂把生理作病理,把养生论误为病因病机论,从而铸成大错,这个大错源出丹溪私淑弟子王纶。而丹溪后学戴、王、汪、虞诸人对此篇的发挥,都没有顾及全文,只是就气血阴阳的有余不足开展争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题目重于内容,形式重于实质,只将鲜明的标题留下深刻的印象,后人更只是借题发挥,不及原意。
其次是对《相火论》的误解。丹溪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内生火热的理论,其以七情释因,伤阴言病机,阴虚阴绝测预后,都与阴虚阳亢之火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也存在虚实性质的本质差别。两篇名论相互映衬,互为说明,更使这种误解根深蒂固了。以知柏苦寒滋阴相指责,便是这一误解之一例。
丹溪治疗思想和养生观点都注重保养气血,而他又以血为阴。把气血论治与养阴理论相混淆,造成了后人对他的第三个误解。气血论治与养阴学说有联系又有区别。营血之与阴精,二者同属于“阴”的范畴,同有滋润濡养的生理作用,又有相似的病因病机特点:其病多见于内伤杂病;积劳久病、房室思虑、失血遗精等等可以成为二者共同的病因;气血久虚易致肝肾阴精不足,阴虚生化乏源亦可致精血不足。但是,气血与阴精二者有先天、后天之异,自不可混淆。赵献可批评丹溪“阴字认不真,误以血为阴”,实际上是对这种误解的批评。赵氏还讲,“读东垣书不读丹溪书,则阴虚不明而杀人;读丹溪书而不读薛己书,则真阴真阳不明而杀人”,可见他把丹溪补气养血观点与养阴学说区分得清清楚楚。这也反证了当时确实存在着混淆气血论治与养阴学说的事实。
还有是对丹溪用药特点的误解。丹溪时代占医界统治地位的《局方》之学,具有温燥辛热的用药特点,这是数百上千年的习惯势力:汉魏以来盛行服食,以温热燥毒为补益,给医界带来恶劣影响。本草十剂有“湿可去枯,紫石英、白石英之属是也”,即以温热石药为滋补肾水,李时珍对此曾有批评。故河间言不可养水以泻火,就是反对“热药补肾水而退心火”的说法的。丹溪激烈反对这种温热辛燥的用药倾向,在实践方面主以甘温滋润如四君四物为补益,理论方面则著《局方发挥》进行了辩驳批判,使医界风气为之一变,也为其后养阴学说的顺利发展清扫了道路。其次,丹溪治病用药法诸家之长而去其短,法河间重泻火又不滥用苦寒,常配合补养剂以免化燥伤阴;师东垣重气血又言东南之人阴火易升,不取风药升阳以免温燥,善配合知柏以降火;法子和善用吐法,又主张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所以,丹溪用药不仅不同于《局方》的温热辛燥,也不同刘、张、李三家之论,自有一种温柔滋润的特色。这不啻是当时医界的空谷足音,说是养阴也未始不可。但调补中州,资气血以化源,自非粘腻之物填补肝肾之阴,毕竟不是“直补真水”,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区别。
这些误解从理论到实践都把丹溪塑造成一个滋阴派的形象,而明代滋阴学说的发展又需要寻求一个有代表性的滋阴派形象和响亮的口号。于是,这种需求促进了误解,而误解满足了需求,结果则歪曲了丹溪的形象。
元代以前滋阴学说已在酝酿发展,丹溪对《局方》的批判更为其壮大完善清扫了道路,阴柔滋润的用药风格又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素材,所以,丹溪之后滋阴学说更有了长足的进步。王纶发挥“阳有余阴不足”而阐述阴虚火动之说,立补阴丸方,首次将滋阴理论与方药直接紧密地结合起来。薛己创真阴真阳之说,用六味丸、八味丸滋化源,开创明代温补一派的先河,其说即附王氏《明医杂著》而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震亨以补阴为宗……虽所用黄柏知母不如后人之用六味丸直达本原”云云,亦指明了朱、王、薛一脉相承的学术思想发展关系。孙、赵、张继而创命门阴阳水火说,最后完成了滋阴学说。汪机发挥“阳有余阴不足”而阐述气血论治,其二传弟子孙一奎与张、赵齐名,同为滋阴说的完成出过大力。可见,最终完成滋阴学说的明代温补学派,似与丹溪势不两立,实际上无论师承关系,还是学术观点上都还有相通之处。
戴原礼、王纶、汪机、虞抟对“阳有余阴不足”的不同理解,形成丹溪后学间的学术争论;而温补派则激烈反对“相火论”和“阳有余论”。这场持续有明一代二百余年的学术论战,把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推上了辩论的风口浪尖,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命题,其中“阴不足”论则为大家一致接受,包括反朱最力的张景岳。“阴不足”的字面意思正体现了滋阴学说的关键内容,而后世争论多停留在命题的字面意义上而不全面考虑丹溪原意。因此,在论战中不断完善的滋阴学说得到了“阳有余阴不足”,“阳非余真阴不足”的命题,这是学术发展的要求,要求一个醒目贴切而又高度概括的口号。丹溪满足了这个需求,同时也加深了后人对他的误解。论战的结果是丹溪登上了滋阴派创始人的宝座,这实是丹溪始料不及的。这是丹溪之学风行江南的结果,也是阳有余阴不足论题被进行了移花接木的改造的结果。自此之后,丹溪的真面目更不为世人所识了,这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造成这场历史误会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以上“四个误解,一个需求”,仅是笔者根据有限资料作了初步分析之后所提出的一个假设。设想可能不尽妥切,根据也不一定充足,论证和推理或有不周,因此仅仅是一个假设,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刘时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