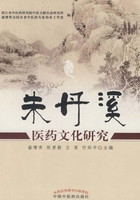
论朱丹溪与理学的关系
朱丹溪生平和理学的关系很密切,要深入和全面地研究丹溪的学术思想,首先要做到知人论世,对丹溪与理学的关系进行一下探索,是有必要的。
(一)丹溪生平和理学的关系
理学,后人或称之为“新儒学”,是我国宋代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它用思辨的形式,研究关于理、气、性、命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用以论证和解释宇宙间万事万物,因而得名。理学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即有名的“宋五子”。理学出现于宋不是偶然的,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理学标志着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宋、元、明整整七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取得了思想界的正统地位。
朱熹作为理学大师,是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遍求周、张、二程诸家的学说,作系统的研究,融会贯通,而集其大成。全祖望说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黄百家说:“其为学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其为间世之钜儒,复何言哉!”(引同上)
丹溪之所以成为理学家,有他的历史、地理背景和家学渊源。
丹溪出身于一个奕世蝉联的读书人家。南宋时,有东堂府君者,名良祐,以六经为教,儒学传家,他是丹溪的五世祖,其后代多以儒学闻名。
元时的金华地区,属浙东宣慰司婺州路。金华地区包括其属县义乌,自何基接受朱熹理学以教授乡里后,成为有名的理学之乡,程朱派的理学十分盛行。朱熹理学的嫡传黄干,曾为江西临川县令,金华人何基奉父命从师于黄干,居金华北山,人称北山先生。卒年八十一,谥文定。这是理学入金华的初祖。北山之传,源远流长。他亲传金华王柏,字会之,号鲁斋。卒年九十八,谥文宪。金履祥,兰溪人,事同郡王鲁斋,从登何北山之门。后居仁山之下,学者称为仁山先生,卒谥文安。许谦,字益之,金华人,长值宋亡家破,不仕,就学于金仁山,学者称白云先生,卒年六十八,谥文懿。《宋元学案》卷八十二为《北山四先生学案》,论列甚详。“北山四先生”后世习称“金华四先生”。明代章一阳著《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萧阳复序曰:“诸儒之说,至晦庵始集其成。勉斋黄氏,亲受业于朱子之门。金华何文定先生,虽后朱子生,而口传心受,得之勉斋。自是而传之王文宪、金文安、许文懿,仅二百年间,四先生踵武相承……生于一郡,相继而兴,所谓文不在兹乎?”许谦即朱丹溪之师。
丹溪年轻时,习举子业,又尚侠任气,不肯出人下。在家庭和环境浓厚的理学空气影响下,三十六岁那年,感到“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以下简称《石表辞》)于是拜许谦为师,接受理学学说。他在理学的涵泳陶冶下,进步很快,日有所悟。常常夜半起身,一卷在手,坐至四鼓,刻苦学习。如此数年后,学业大进。
朱丹溪素怀惠民之心,所谓“不为良相,必为良医”,原是历代读书人的理想。而直接促使他学医的是他的母亲和老师许谦的疾病。许谦对他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于是丹溪尽焚以往所习之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后师从当世名医罗知悌。“罗名知悌,字子敬,世称太无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学精于医,得金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然性褊甚,恃能厌事,难得意。翁往谒焉,凡数往返,不与接。已而求见愈笃,罗乃进之曰:‘子非朱彦修乎?’时翁已有医名,罗故知之。翁既得见,遂北面再拜以谒,受其所教。罗遇翁亦甚欢,即授以刘、张、李诸书,为之敷扬三家之旨,而一断于经。”(《丹溪翁传》)丹溪从罗知悌学一年,尽得其传。
朱丹溪既得朱熹五传之理学,又师从当世名医罗知悌,得继承金元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医学之真传,理学、医学,遂两造其极。第一个把理学思想引入医学领域,并取得很大的成果。
(二)丹溪学术思想和理学的关系
丹溪学术思想的主要来源,是远绍《内经》,而寻其指归;近承河间,旁通子和、东垣三家,而极其变化;复参之于理学之说,融会贯通,形成一家之言的丹溪之学。
丹溪学说的重心,是有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这两论的哲学基础,又和理学的“主静论”有关。要透彻理解其渊源所自,必须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说起。“太极”这个名词首见于《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指天地,“太极”表示宇宙万物最根本的来源。古代哲学家对太极并没有加以特别的重视。到了宋代,理学的先驱者周敦颐著《太极图说》,成为理学本体论的中坚,“太极”一词,乃变成哲学界的热门话题了。
《太极图说》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此一节前后还讲到“无极”,朱丹溪把理学中“太极”的概念引入医学时,不采取“无极”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后来的医家,也基本上不取“无极”之说,故这里从删。)《太极图说》以“太极”统阴阳、五行,有它的合理性;阴阳动静、互为其根的思想,也比较深刻。它进入医学后,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促进了医学理论,特别是命门学说的研究,把阴阳水火气血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丹溪《相火论》从凡动皆属火,人为物欲所感,不能不动,动则相火易起入手,论证“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预防之方,不外乎周敦颐“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熹“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丹溪认为,这才是“善处乎火者”。做到了“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待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何贼之有?”这是丹溪《相火论》的主要观点。
丹溪从天地阴阳之理,及人体生长发育的事实出发,说明阳有余、阴不足。接着就逻辑地回到了同一个主题,即:阳既有余,如不能主之以静,则相火易于妄动;相火妄动,则消耗不足之真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为养生之大戒。故丹溪屡屡戒人勿妄动相火,其中尤以色欲为甚。他说:“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阳有余阴不足论》)
丹溪还吸收了程朱理学有关天理人欲的观点。程朱主张用天理来克服人欲望,用道心来主宰人心。朱熹说:“人之一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他举例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丹溪结合到医学上,在养生方面,提倡节制性欲,节制饮食,著《饮食箴》《色欲箴》。
理学关于太极动静、天理人欲的学说,有浓厚的禁欲主义和宗教精神,运用于社会人事上,有很大的消极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把它引入医学后,由于医学领域里矛盾的特殊性,却取得了好多积极的成果。如养生方面提倡静心息虑,节制性欲、饮食,使人体生命活动的节律不致过快;在治疗上谆谆以资化源、养阴精为言,用四物知柏滋阴降火,发展了养阴的治疗方法等。这些方面,无疑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
(三)丹溪治学方法和理学的关系
丹溪的治学方法,继承了以朱熹为集大成的宋学传统。他用宋儒治经之法研究《内经》《伤寒论》,开明清倡言错简一派的先河。他又著《局方发挥》,促进了医学领域的百家争鸣。下面分述之。
1.治经倡言错简 宋学和汉学,在治学方法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说:“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有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这和汉学的学风“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两者的不同是很明显的。
丹溪学医,首治《内经》,对《内经》最有研究。《格致余论》有一篇《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辨》,辨正王冰章句注释之误,并进而对本文有所移易订正,卓识宏论,深得经义,学者因之尚可略窥丹溪治《内经》的方法。他说:“《内经·生气通天论》病因四章。第一章,论‘因于寒,欲如运枢’以下三句,与上文意不相属,皆衍文也;‘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两句,当移在此。第四章,论‘因于气,为肿’,下文不序病证,盖是脱简。‘四维相代’二句,与上文意不相属,亦衍文也。”
于此可知,丹溪治《内经》,倡言错简,衍文删之,错简乙之,孰为文字之脱讹,孰为注释之错误,皆直斥不讳,这正是嗣宋儒治经的宗风,和以前医家随文训释,注不破经的方法是大相径庭的。
他十分推崇仲景的《伤寒论》,但也不放过它的“错简”。戴良《丹溪翁传》载:“罗成子自金陵来见,自以为精仲景学。翁曰:‘仲景之书,收拾于残篇断简之余。然其间或文有不备,或意有未尽,或编次之脱落,或义例之乖舛,吾每观之,不能以无疑,因略摘疑义数条以示。’”疑义数条,具体内容如何,传既未载,不得而知。他有《伤寒辨疑》一书,惜亦不传。然书名“辨疑”,其内容当亦不外乎辨《伤寒论》中“文有不备,意有未尽,编次脱落,义例乖舛”之类。以上可见丹溪治经不偏信盲从而能倡言错简之一斑。
2.推动学术争鸣 丹溪早年学医,已致疑于《局方》,觉悟到株守《局方》,“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丹溪翁传》)。晚年更著《局方发挥》一书,对《局方》恣用香燥热药,忽视辨证论治:风病、痿证,混同论治;泻利、滞下,一体温涩的缺点,进行了批评。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丹溪“于《局方》之多用温补燥烈之药而耗散真阴者,尤辨之恺切详明,足与其《格致余论》相辅而行。从此医家之分别门户以相攻击者,自此书始。盖其儒学本渊源于朱子,故仿朱子《杂学辨》例以著书也。”按:《杂学辨》一卷,朱熹撰,内容系指斥当代诸儒之杂于佛老者,包括苏轼、苏辙、张九成、吕希哲等人的学说。朱熹好辨,以卫道为己任,他与陆九渊辨太极、与陈亮辨功利,是思想史上有名的两次学术争鸣。丹溪在这一点上,受到朱熹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丹溪之后,医学领域里百家争鸣逐渐盛行。他的弟子王履著《医经溯洄集》,继承其师的治学方法,以好辨著名。明清以来的医学大家,如张景岳、喻嘉言、徐灵胎、陈修园,以及诸温病大家,对前人学术思想,往往或申或驳,并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在著作中,他们几无一不是以学术争鸣的面目出现的,这和汉唐时代医家述作之风是多么的不同。
结语
丹溪由儒而医,第一个把理学学说引入医学,促进了医学理论中阴阳水火气血之辨的深入研究,是《内经》以后哲学与医学的又一次结合的开始(第一次是朴素的辩证唯物论——阴阳五行学说和医学的结合),其影响是深远的。
丹溪用宋学家法,研究《内经》《伤寒论》,开倡言错简一派。他著《局方发挥》,对医学领域里的百家争鸣,起了推动作用。
理学影响了丹溪的一生,他为学一以躬行为本,操履笃实,内外一致,可以说是理学的实践家。他决定以医为终生职业,其中一个原因是受了许谦的影响,而他行医的宗旨,则是否“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戴良《丹溪翁传》),不是仅为稻粱谋。正因为他有理想,有目的故能勇猛精进,百折不挠。丹溪成了名医后,“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夫告痛,先生谕之曰:‘疾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勿惮也”(见《石表辞》)。真是仁人之言蔼如,虽千载之下,尚想见其为人,使人自然产生高山景行的感觉。这一切是和他的理学思想分不开的,总的说来理学对他的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
总起来说,丹溪把理学引入医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徐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