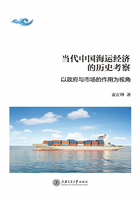
第二节 国际海运:离不开市场机制
中国在完成“三大改造”之后,走上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道路。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海运经济,学界较多地关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的作用,而忽视了国际海运 市场下市场机制的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研究的视野仅局限于国内,还没有扩展到国际海运范畴。海运经济的国际性特点显著,尤其是远洋运输离不开国际交往,中国的海运经济在国内受政府干预的同时,在国际上还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在国际市场上租用船舶、购买船舶和使用外国班轮是该时期中国在海运计划经济外主要的市场行为,租赁价格、船舶价格和运输价格深受国际市场机制的影响。
市场下市场机制的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研究的视野仅局限于国内,还没有扩展到国际海运范畴。海运经济的国际性特点显著,尤其是远洋运输离不开国际交往,中国的海运经济在国内受政府干预的同时,在国际上还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在国际市场上租用船舶、购买船舶和使用外国班轮是该时期中国在海运计划经济外主要的市场行为,租赁价格、船舶价格和运输价格深受国际市场机制的影响。
一、船舶租用
在对外贸易运输中,按运输实施者划分一般分为我方派船和对方派船两种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海运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功能不够完善,对外贸易运输多数由对方派船完成。因此,争取派船的主动权成为中国对外贸易运输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强大的海运供给能力。但是,中国海运事业处在起步阶段,自身供给能力薄弱,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的船舶数量都很少。在中国造船工业落后的背景下,短期内提高海运供给能力唯有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租用船舶和购买船舶。
最初,中国通过两个途径在国际市场上租用船舶:一是借助苏联和东欧国家与资本主义租船市场的业务关系,由它们代理中国向资本主义国家租船;二是通过中国在香港设立的海运机构和企业,由它们代理中国向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北欧国家租船。这时的对外租船业务呈分散状态,各个外贸公司、交通部所属单位和外贸部门所属运输机构等都各自开展租船业务。这种分散租船的做法,具有灵活性,给予外贸企业运输的自主权,外贸企业可与船主直接联系商议价格。
1955年5月,中国作出规定:凡是外贸公司的货物运输都必须委托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处理。这项新规改变了以往各外贸公司运输业务“各自为政”的做法,把外贸运输工作完全集中在一个机构统一办理。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对外也称中国租船公司,统一负责中国外贸运输的租船业务。它的性质属于船舶经纪人,它以独立法人的资格在国际租船市场开展业务。
1956年底,中国租船公司加强了与欧洲的联系,并与英国的怡和公司和伦巴公司两家租船经纪公司建立了租船代理关系,进一步扩大与国际租船市场的业务关系。50年代的租船年平均租船量为287艘次,273万载重吨。租船的最高年份1960年,租船量359艘次,361万载重吨。
1961年4月,中国远洋运输公司 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着力发展自营远洋船队。虽然在60年代对外贸易的运输主要由中方派船,但由于中国组建远洋船队起点低,船队运力薄弱,因此我方派船当中大部分是租用的船舶。从1961年至1970年看,远洋国轮承运量占中方派船海运量的比例虽然逐渐有所上升,从1961年的6.1%上升到1970年的21.3%,但绝大部分外贸物资仍须租船承运,到1970年租船承运量仍然占中方派船海运量的78.7%(见表1-1)。
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着力发展自营远洋船队。虽然在60年代对外贸易的运输主要由中方派船,但由于中国组建远洋船队起点低,船队运力薄弱,因此我方派船当中大部分是租用的船舶。从1961年至1970年看,远洋国轮承运量占中方派船海运量的比例虽然逐渐有所上升,从1961年的6.1%上升到1970年的21.3%,但绝大部分外贸物资仍须租船承运,到1970年租船承运量仍然占中方派船海运量的78.7%(见表1-1)。
表1-1 1961—1970年中国外贸海运船舶使用情况表

资料来源: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现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229-230页。
20世纪60年代的年平均租船量为512艘次,600多万载重吨。租船最高年份为1967年,共租船642艘次,739万载重吨。虽然租船承运量占中方派船海运量的比例在下降,但是从租船的载重量来看,60年代的租船量比50年代增长一倍有余。
20世纪70年代,年平均租船量为367艘次,644万载重吨。1973年底,中租公司拥有期租船362艘,近600万载重吨,是拥有期租船的最高峰。这时,期租船开往五大洲的班轮有24条航线,可接受货载的基本港口190个,转船港口约350个,它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进出口任务的完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中国船队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是,就在1973年底前后,进口货运计划突然变更,货运量大幅度削减,以致期租船大量过剩。为了不使船只闲置而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大力向国际市场进行转租。从1973年底到1975年两年多时间中,计转租期租船171艘次,367万载重吨;转租程租船122艘次,296万载重吨。总的来看,70年代租船占中方派船海运量的比例继续下降,1977年仅占11.7%。
二、船舶购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造船工业恢复较快,各国均在努力扩大本国的商船队,从1948年到1964年,世界商船队总吨位由8030万吨增至15260万吨,增长近一倍。但在运力迅速猛增的同时,海运危机已在潜伏。1956年以后,世界造船能力过剩30%至40%,国际船舶市场的船价开始跌落,延至60年代初期依然不能复苏。据当时英国航运界统计,1960年全世界闲置的船舶总吨位达500万吨,1962年更是与日俱增,以该年的6至8月为例,闲置船舶的发展趋势颇具代表性(见表1-2)。
表1-2 1962年国际海运市场船舶闲置概况表

资料来源:朱士秀:《招商局史(现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由于船舶闲置量猛增,一方面造成旧船价连续暴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建造的万吨自由轮,售价跌得更低。1956年售价为650万英镑,1961年12月跌至12.5万英镑,1962年1月降至9.25万英镑,3月更跌到8.5万英镑,6月仅为6.5万英镑;另一方面,抑制新船的产量增长,使造船工业面临严重威胁,纷纷降低购船的条件,新船船价也在下降。
国际船价的暴跌为中国购买船舶以提高海运供给能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自1949年以来,中国远洋运输的运力供给主要依赖外国。直到1961年4月27日,成立了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和中远广州分公司,才宣告结束中国无远洋船队的历史。但是这支远洋船队不仅起步晚,而且起点低,到1962年仅有5艘船,3.4万载重吨,年货运量仅14万吨,不及当年中国海运总量的1%。 长期依靠对外租船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对外贸易和交往的掣肘,因此,国家决定通过向外购船壮大国有船队以提高自己的海运供给能力。
长期依靠对外租船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对外贸易和交往的掣肘,因此,国家决定通过向外购船壮大国有船队以提高自己的海运供给能力。
1963年,招商局经国务院批准率先在香港购买船舶。位居香港的招商局在瞄准国际海运市场行情之后,利用船舶营运收入和招商局利润共计5017777港元,购进了3艘万吨级船舶。从此之后,鉴于招商局位居香港的有利条件,可随时注意掌握世界船舶市场的行情,及时收集船舶信息,交通部委托招商局协助有关部门办理购买远洋船舶事宜。1964年,中国利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外汇贷款从英国、挪威、利比里亚购进远洋船舶7艘,合计63096总吨,共达89094载重吨,船价总共467.8万英镑,其中利用贷款为342.5万英镑。这是中国首次利用贷款购买船舶。
从1963年至1969年,交通部共购买远洋船舶18艘(其中新船7艘),23万余载重吨,总值3377万美元。到1969年底,中国远洋船队已拥有船舶70艘,77万载重吨,其中1/3系我港澳银行吸存的外汇资金所购买,由于船队营运效益好,还款较快。但是,此时的中国自营远洋船舶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外贸运输的需要。中国远洋船队只能承运进出口物资10%左右,其余仍靠租船,每年租船费用达1.3亿美元之巨。
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力争在1975年在远洋运输方面基本上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国家计委明确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把中国的远洋船队从100多万吨发展到420万吨。
1972年,世界船舶市场行情看跌,由于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各国纷纷采取关税壁垒政策,限制进口和增加进口关税,导致国际间的货运量剧减,使国际海运界受到沉重的打击,运价、租船费用和船舶买卖价格连续下跌。加之,70年代的远洋船舶已开始向大型船、快速船、集装箱船和子母船的方向发展,那些船龄大、吨位小、航速慢的船舶逐渐被淘汰,大批旧船涌向二手船市场,加剧了国际船舶价格的下跌。以8500吨至1.5万吨干货船为例,1972年与船价高峰期的1970年第三、四季度相比,1950年至1955年建造的船舶售价下降67%;1956年至1959年建造的船舶售价下降45%至55%;1960年至1961年造的船舶售价下降30%至50%。
招商局利用国际海运市场船价疲软之机,共购进二手船94艘货轮,款价6000万英镑。其中油轮2艘,39590载重吨;散装船13艘,314317载重吨;9000吨以下中型船舶17艘,11.19万载重吨;干货船(9000吨以上)62艘,729156载重吨。
1973年和1974年,出现国际性物价飞涨,加之在世界范围内抢运粮食与燃油,能源危机导致石油售价和运价均上涨,海运业因之一度兴旺,旧船抛售少,价格高,出现了同1972年截然相反的局面。因此,这两年的购船数量相对减少。1973年购进船舶60艘,共106万载重吨;1974年购进船舶14艘,共681550载重吨。
此后的1975年和1978年,国际海运市场出现严重的萧条局面,货运量下降,船舶过剩,船商竞相抛售船舶。这一形势对中国购船十分有利。招商局抓住有利时机购进大批船舶,1975年共买船52艘,1166658载重吨;1978年购船数量为历年之冠,共成交102艘,共计2402206载重吨。
经过十余年的购船,中国远洋运输能力迅速增强,1979年远洋船舶拥有量为1970年的9.4倍。1961年之前,由中国派船承运的外贸货物,除利用中外合营公司的船舶承运10%以外,其余全靠租用外轮承运。1971年国家远洋船队成立后,年货运量不足中方派船运量的28.6%,到1976年,远洋国轮就已经承运了外贸货物中方派船运量的70%左右,结束了外贸海洋运输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历史。
从中国向外购船的过程来看,其特点是首先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然后选择在国际航运市场低迷的时机购船。海运中船要素不仅在国内受政府干预通过计划手段进行配置,但同时也在国际上通过市场手段进行配置。中国海运供给受到国际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的影响,体现出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特点。
三、运价博弈
班轮运输是国际海运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具有定船期、定港口、定货载、定航线的特点。开辟班轮航线需要有稳定的货源以及足够的运力。在该时期,中国还不具备开辟国际班轮航线的条件,仅开辟不定期航线。中国的班轮航线船期为外国所把持,直到1974年,承运中国进出口货物的班轮仍然全部是外轮。中国至东南亚、孟加拉湾、巴基斯坦、波斯湾等航线由新加坡、香港侨资及日本、巴基斯坦等7家班轮公司承运,中国至东非、西非、地中海、西北欧、南太平洋、东加拿大等航线由日本、南斯拉夫、联邦德国、荷兰、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的8家班轮公司承运。 该时期由于中国使用外国班轮数量较多,国际班轮运价对中国的海运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时世界班轮运价被班轮公会操纵,形成垄断价格,在华的外国班轮运价也不例外。面对处在垄断状态的国际海运价格机制,中国实施政府干预与班轮公会展开了一场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运价博弈。
该时期由于中国使用外国班轮数量较多,国际班轮运价对中国的海运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时世界班轮运价被班轮公会操纵,形成垄断价格,在华的外国班轮运价也不例外。面对处在垄断状态的国际海运价格机制,中国实施政府干预与班轮公会展开了一场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运价博弈。
在1949年以前,班轮公会控制着世界主要海上航线的运输,排挤非会员公司,垄断货运,因此国际贸易的海运运价一直被它所控制。例如中国至欧洲的航线被伦敦远东班轮公会控制。它们排斥非公会班轮,实行双重费率制,控制货源,抬高运价,牟取暴利。例如承运中国广州出口陶瓷去西非的班轮运价比承运日本同类出口货的班轮运价高出15%,而后者航程远于前者,致使广州陶瓷价格缺乏竞争性而无法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沿海主要港口的外国班轮公司直接向我各进出口专业公司揽货,与班轮公司相比,中国的外贸公司犹如一盘散沙,分散的货主无力抗衡团结的班轮组织。因此,沿用原来班轮公会的运价制度。尽管中国政府多次与班轮公会交涉,但迫于自身的海运力量弱小,加之受到封锁禁运,不得不暂时接受班轮公会的高运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沿海主要港口的外国班轮公司直接向我各进出口专业公司揽货,与班轮公司相比,中国的外贸公司犹如一盘散沙,分散的货主无力抗衡团结的班轮组织。因此,沿用原来班轮公会的运价制度。尽管中国政府多次与班轮公会交涉,但迫于自身的海运力量弱小,加之受到封锁禁运,不得不暂时接受班轮公会的高运价。
班轮公会控制下的中国海运价格已经不受国际海运供求的影响。例如1957年国际海运市场不景气,运价普遍下跌。但是,班轮公会为了转嫁海运危机,对中国的运价不仅不降,反而上调,致使中国外贸运输成本增加。海运运价逆市场行情而行的机制严重阻碍了中国海运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政府采取干预的政策对付之。
早在1956年2月,为了统一步调一致对外,中国外贸部和交通两部发布了《关于统一租船、订舱的联合指示》,规定中国外运公司接受各外贸公司委托,统一掌握外贸进出口货源,统一对外租船、订舱、负责完成外贸运输任务。中国船舶向外国出租与租用外国船舶航行中国,均须通过中国外运公司办理。中国外轮代理公司以外籍班轮公司在中国港口代理人的身份,向中国外运公司揽货,中国外运公司根据交货条件向中国外轮代理公司订舱。 这个规定,实际上是由中国外运公司统一管理货代业务,由中国外轮代理公司统一管理船代业务,标志着中国从班轮公会收回中国对外运输的货代与船代业务权。同年4月,中国沿海主要港口成立了运价小组,负责调查搜集资料,研究世界海运运价和费率,提出新运价。
这个规定,实际上是由中国外运公司统一管理货代业务,由中国外轮代理公司统一管理船代业务,标志着中国从班轮公会收回中国对外运输的货代与船代业务权。同年4月,中国沿海主要港口成立了运价小组,负责调查搜集资料,研究世界海运运价和费率,提出新运价。
1958年2月12日,中国各港口的外轮代理公司在同一时间向来华的班轮公会会员公司的船舶正式宣布:废除班轮公会载运中国货物使用的运价表;接受并执行中国制定的运价表。对外轮在货载安排上作出优先次序:侨商、华商船舶为先;非班轮公会船舶次之;接受中国运价表的班轮公会船舶最末。
中国的运价新规在日本和东南亚航线很快奏效,远东班轮公会日本航线的会员立即接受中国制定的上海至日本的运价,从而使这一航线的运费平均降低32.86%,东南亚航线的有关船公司也摆脱了班轮公会的控制,同意实行中国制定的费率,使运费平均降低42.96%。上海港迫使6个拒不接受中国自主运价的班轮公会从上海港所有航线撤出,在7条航线上争取到了自主运价权,为国家节约了44.96%的外汇运价支出。广州黄埔港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航线的运费降低40.22%;黄埔港至印度尼西亚航线的运费降低44.25%。
在欧洲航线上的运价博弈相对复杂。在中国提出运价新规一年之后,班轮公会才宣布中国至欧洲的班轮运价降至30%。尔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已降低的运价在1961年和1962年又两次上涨。1964年由于海运形势好转,班轮公会又提出进口货运上涨14%,出口货运上涨12.5%。但是,中国的强硬态度迫使班轮公会内部发生分化,其中由英国的红烟囱轮船公司和蓝烟囱轮船公司、丹麦的宝隆轮船公司、瑞典的东亚轮船公司、挪威的威廉臣公司、荷兰的东亚公司、西德的苏埃德轮船公司共同组成“中国运费协议组”,于1964年7月17日来华同中国租船公司、中国外轮代理总公司洽商运价,最后确定进出口货物的运价各涨6%。
中国政府力量的介入一方面能有效抗衡国际海运垄断组织;另一方面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中国的运价管理违反了运价应当随行就市的原则,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使外国班轮有时无法维持其航线。与班轮公会的运价相比较,中国运价既缺少灵活性,又受到行政干预,不能随国际航运市场的变动随时作出调整,因此与公会运价差距越来越大,有时竟低60%~70%。这就形成与班轮公司的矛盾日益激化,使得班轮公司的航线过多地退出中国。
1965年,航行中国港口的外国班轮公司有24家,每月平均20艘次,航行9条航线。1966年至1970年间,上述9条航线上,有10家班轮公司的15条船中断了航行中国的业务。为了适应对西方国家贸易的需要,在这时期中外运公司又相继与5家班轮公司建立了新的业务关系。1973年又有8家班轮公司中断了中国航线。
造成外国班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班轮公会展开价格博弈过程中为了争取价格的主动权而过多地采用政府干预手段,使得运价偏离国际海运市场行情。航行中国的班轮运费普遍偏低,赶不上国际航运市场运费水平。根据1974年资料统计,班轮航行香港的运价与航行中国港口的运价比较,从香港往澳大利亚发货比从国内往澳大利亚发货要高出54.7%;同样到新西兰高62.5%;到新几内亚高48.3%;到孟加拉湾高90%;到卡拉奇高68.6%;到西非高60.5%;到红海高114.6%;到新加坡高90%。因之,许多外国班轮公司认为经营中国航线无利可图,一致要求提高运价;有的班轮公司甚至表明,如果不能提高运价就不再来中国港口,而到香港去接运中国出口货。 中国在与班轮公会的价格博弈中取得了胜利,掌握了运价的决定权,但是同时也因矫枉过正而阻碍了中国的外贸运输。
中国在与班轮公会的价格博弈中取得了胜利,掌握了运价的决定权,但是同时也因矫枉过正而阻碍了中国的外贸运输。
从这场中国与班轮公会长达二十几年的运价博弈来看,国际市场机制与国家政府干预都存在各自的缺陷,需要二者相互制约达到均衡。一个不是封闭的国家,其海运必将受到国际市场机制的影响,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兼而有之,政府干预是消除负面影响的必要手段,但是政府干预要适度才能实现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