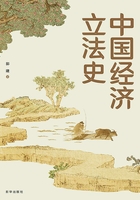
第四节 两税法时期
唐朝租庸调制破产后,统治者施行了按人户资产和按地亩征收赋税的“两税法”,之后“两税法”又被宋朝继承。元朝及明朝初年虽不以两税为名,但仍保持着两税法“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的原则,以及不再规定全国统一的税率、税额。赋税分夏秋两季征收等原则,因此仍可将其视为两税法的余绪。两税法共延续了七百多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背景下,直接征发农民劳动力的徭役不再是主要剥削方式,各种力役转变为以钱代役,进而转为赋税。赋税的实物比重大为下降,而货币比重大为上升。
唐朝两税法
唐朝在建中元年(780年)正式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法,实行了税制大改革。唐朝的两税即指地税与户税。地税与户税都在唐初甚至在隋代和北朝就已经出现,只是当时是杂税,后来变为主税而已。地税,原来是作为防备荒年而征收的“义租”。北齐租调制之外,规定每床、每头牛必须纳义租五斗。唐初贞观年间,唐太宗下令:“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以后曾一度改为按户出谷。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正式规定地税按亩征收:“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收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地税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义租,到了朝廷财政困难时,就变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正式税收了。
户税原是一种按户等征收的货币税,以供给文武百官的俸食余钱,以及传驿、邮递等费用。唐初,一年户税总额仅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贯。户税是租庸调实物之外朝廷最重要的货币收入。因此户税逐渐走向正规化。武则天统治时强调:“诏天下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税户。”开元时,正式规定户税定额:“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
户税与地税的特点都是按户征收,王公以下文武百官权贵也无免税特权,征收的面广。而且无论是否拥有土地,有户有资则有税。当均田制遭破坏后,封建王朝无法直接控制土地与农民人身时,这两种资产税的作用就日益显著。盛唐天宝年间(742—755年),地税年收入已达一千二百四十多万石,而当时租庸调正税中的丁租一年才一千二百六十万石。户税在天宝年间的年收入也达二百余万贯,以开元年间(713—741年)的绢价每匹二百一十文计算,户税相当一千万匹绢,而当时正税的庸调总共才绢七百多万匹、布一千三百五十多万端。因此在安史之乱后,户税、地税取代租庸调已是必然趋势。
唐大历四年(769年),朝廷下令,将地税、户税整齐划一。规定地税分春秋两季征收。“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户税则王公以下,“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官员也没有免税权,凡现任一品官按上上户纳税,九品官按下下户纳税,余品依此类推。如果一户之中数处任官,每处依品纳税。对于工商业者,如有邸店、行铺、炉冶,原来必须加二等纳税,现改为仍按原户等纳税。凡是无土地的“寄庄户”,从原八等加至七等;无户籍的寄住户,从原九等加至八等。户税是一种资产税,以产业为准,“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纳税”。军队将士庄田,予以优待,“并一切从九等输税”。
唐建中元年(780年),朝廷正式实施两税法,废除原来的租庸调。两税法成为主要赋税种类,其规定:征收两税以人户、资产为准,“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人,以贫富为差”。无论过去是何地籍贯,即就现居之处造簿登记纳税。不住一地的行商,“在所州县,税三十分之一”。即在收税时经过的州县税三十分之一的资产税。征税时间:“夏输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税额不再固定,“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每年由主管部门造出预算,以一年支出(包括所需要的劳动力,也折合成雇工工钱)定额平摊各地。征收的品物、地税仍为实物。“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实际上是将原先调、庸定额折钱摊入两税。然而户税征钱,地税征粮只是原则规定,实际上仍有征发各项实物,“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除了两税之外,取消一切杂徭、杂役、杂税。“敢加敛,以枉法论”。由于两税法是先问现居之户,后问所有之产,因此户籍是重要的依据,仍强调“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在定户等时,为了手续简便,普遍采取“手(首)实”,即由每户自报家产的方法。
两税法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两税法实质是征收资产税,封建国家的剥削对象从人丁,即对农民劳动力进行直接剥削转向按私有财产的单位户资、地产进行间接剥削。按资产收税,改实物为货币,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并且取消了无偿征发力役,徭役向赋税转化。就制度上而言,两税法具有税种划一、手续简便等优点,对于纳税人、纳税时间都有明确规定。其缺点则在于先定税额后定税率,各地负担不均,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不可能做出精确的财政预算,并为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提供了方便。估定户等和评价资产没有科学、客观的方法,正如当时人陆贽所批评的:“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两税法规定一切以货币计算纳税,而当时社会商品货币经济还不够发达,政府需要的物资不可能全由市场获得,必然还要征收实物。造成以实物折为钱币(计资定税),征收时又将货币折成实物,几经倒腾,农民负担大为加重。
宋代两税法
唐代灭亡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混战不已,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宋朝统一全国后,继承五代军阀横征暴敛的种种制度,并不加以整理,照旧征收,税制极为混乱。
宋朝名义上继承了唐代两税法,但将户税与地税合并于一,专以土地为征税对象。税率名义上是“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征收时间是夏钱秋米,两次征收。因此宋代两税已成夏、秋两税了。至此,两税从原来的土地、资产税合并为单一的土地税。
宋代除了两税之外,各种杂税、附加税层出不穷。主要有如下税种:
1.农器钱。五代时曾规定农器由官府专卖。宋代改为由民自造,但必须纳税钱,按土地每亩征一文五分。这项杂税直至北宋中期才废除。
2.牛革筋角税。五代严禁牛皮、牛筋、牛角出境(牛皮为制甲胄原料,筋、角为制造弓箭原料),全部收官。以后改为随两税征收,每土地十顷纳牛革筋角一副。这一杂税至南宋才废。
3.头子钱。这是两宋最主要的附加税之一。宋初规定川陕地区输两税时,夏钱每贯多征七文零头以弥补仓储运输的损耗,以后推广至全国。南宋时,头子钱每贯达五十二文。
4.义仓税。这是两税中的地税,原来从备荒义租演化而来,五代时又重收义仓税,宋代仍沿用之。宋初规定每纳两税一石,增纳义仓税一斗。两宋时期,义仓税废置无常。
5.进际税。它是专征于两浙地区的一种附加税。原割据这一地区的钱氏吴越国,为向宋朝进贡而征收进际税,宋朝吞并吴越后,照收不误。每田十亩,虚增六亩,每亩纳绢三尺四寸,米一斗五升二合。每桑地十亩,虚增三亩,每亩纳绢四尺八寸三分。这一附加税种直至南宋仍在征收。
6.和买。它是两宋扰民最甚的杂税之一。和买原是政府向民间征购绢帛的意思,唐代已有此项制度。每年春季,农民困乏之时,官府预先付给绢帛款项(实为一种放贷),至蚕茧上市,农民以绢帛偿还,故称“和买”或预买。北宋中期开始,官府不再预付款项,而至秋却仍向农民征收绢帛,成为勒索杂税。到了南宋,又改为征钱,称“折帛钱”,每匹折钱两千文。
除了以上之外,尚有鼠雀耗(每百石加输二斗)、省陌(官府征钱以八十钱为一百钱,官府贷放钱而以七十七钱为一百钱)等名目。因此宋朝人称“两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
宋代两税在征收制度上也是征出多门,成为变相的杂税、附加税。比如:
1.折变。两税规定是夏钱秋米,而官府往往“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每当官府需要某项物资时就下令将钱、米改折他物缴纳。而折变时的物价又全凭官府指定。
2.支移。原来两税法规定,人户原则上向本地官府缴纳两税。宋代则规定,官府可因需要令百姓自行将两税输往外县。习惯上输甲地,又往往令改输乙地。百姓除两税之外还要负担运输,苦不堪言。北宋中期规定:“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如不愿意自己运输,即向官府缴纳“支移脚钱”,成一种附加税。到南宋,支移一般都改为征收脚钱,往往一石税粮要纳脚钱三斗七升。
3.预借。唐代已有“青苗钱”,在春天青苗时即预征两税。宋代预征已成惯例。往往有预征三四年、七八年以后的两税。有的前任官员已预借,后任官员再预征,成为一大弊政。
宋代两税法已把户税并入了地税,因而又在两税之外征收人头税,称之为“身丁钱米”。凡江南、两浙、湖南、岭南人户,男子年20为戍丁,每年向官府输身丁钱米,至60岁年老而免。这项人头税税额不固定,沿袭五代割据政权的混乱局面。两浙每丁身丁钱三百六十文;福建、两广则征收身丁米。
宋代职役
古代徭役制度经北朝隋唐,兵役从徭役中分出。以后两税法实行后,直接征发力役也改为征收赋税。就法律而言,役并于税。在古代徭役制度中,剩下的是由各地方政府征发的杂徭,以及为各阶层贵族官僚提供使令、打杂、当差的“色役”。宋代的徭役即主要是指从唐朝色役转化而来的职役。
宋代职役是以地方公职为主的。宋以前县以下的乡土地方公职,是一种“乡官”,号称:“天子之与里胥,其贵贱虽不侔,而其任长人之责则一也。”里胥可以经一定年限推举为官,是宋以前官员的主要来源。唐宋时期科举选官,乡官不受重视,逐渐由身份权利而变成了挨户承担的义务。宋代这种职役主要有:
1.衙前:主管官物、管理州郡仓库、搬运官物、迎送官吏等。押运官物、管理官物如有失落,必须负责自行补足赔偿。
2.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课赋役,清查户籍等。
3.耆长、弓手、壮丁:巡缉乡里,逐捕盗贼。
4.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等:给官府打杂,应付各类使令。
职役之外,还有差役,为各级地方官府充当侍从等。
唐代每三年排定户等为征收两税,而宋代两税落于田亩,排定户等主要是为了征发职役、差役。宋代户等评定,乡村实行五级户等制,实际上是将唐代的九级户等中上四等作为职役的主要承担者,而下五等并为一等,可以免职役。凡职官户、城郊户(城市居民)、鳏寡户、女户、单丁户均可以免役。
由于宋代职役、差役制度不全,曾多次反复。至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推行“雇役法”(或称免役法、差役法),以前承担各种职差役的民户,出“免役钱”,而以前免役的官户、场部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等也得按户等缴纳“助役钱”。官府用免役钱、助役钱雇人充役。免役钱、助役钱随同夏秋两税征收。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又一次将徭役转为赋役。因王安石变法几经上下,雇役法也兴废不时。最后南宋时,职役中的衙前、户长等永为雇役。但其他职役改换名目依然存在,而民间免役钱、助役钱早已成为杂税,不管是否服役依旧征收不误。
辽、金、元赋税
契丹族的辽朝、女真族的金朝、蒙古族的元朝,在建立国家之后,都仿照汉族地主阶级国家剥削方式,建立赋役制度,一般制度上都仿照宋朝。
在田赋两税上,辽、金、元三朝都仿照宋朝夏秋两税制,但制度比较混乱,视各地情况、民族成分而有所不同。如金朝对女真户征收“牛头税”,按耕牛头数征收,每三头耕牛为一具,每具缴纳五斗(后改为三斗)粟米,牛头税比之两税要轻得多(每亩约合五分之一升,而田赋秋粮一亩约五升),以保护女真贵族官僚地主的利益。元代在中原地区征收丁税、地税,每丁纳粟三石,驱丁(奴婢或农奴)一口一石,此为下税;每亩纳粟三升为地税。元代在江南则仍按南宋旧例征收两税。
在户税方面,元代实行科差制度,以人户为单位,征收户钞、包银、丝料。又因户籍之不同而分别立制,致使赋役极为复杂。大概而言,中原地区征收包银,每户纳官银六两。又规定汉族居民还必须向国家及其封主(蒙古王公)缴纳丝料,一般每户一斤六两系官丝,并缴纳若干定额不等的“五户丝”给封主。江南地区征收包银、户钞。包银每户二两,户钞(即中原之五户丝折钞)定额不等。科差一般限于夏秋之际征收。凡儒士、军户、站户、僧道等可免科差,但地税不免。元代的科差沿袭了蒙古军队军事统治时期的苛法以及金和南宋的一些搜刮方法,因而并无统一的原则、制度可言。包银至元末泛指一切杂税。
元代在徭役方面制度称为差役,也与宋代一样以职役为中心。各地凡有纳秋粮一石以上者,皆编为里正(每乡一人),主首(乡以下每都二至四人),每年轮流负责为官府催督赋税。如有缺损,必须补赔。为防盗贼,每二十户设立巡防乡手,遇盗,立期限盘捉(一日为一限)。巡防乡手由各色户等中每一百户出一人担当。此外,还有催督农耕的社长等。职役之外,由地方政府征发的力役杂徭统称“杂泛差役”。
明初赋役
明朝建立后,对于赋役制度本身并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基本上仍沿袭宋元之旧。只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推行了较为彻底的户口清查与土地清丈,在此基础上整顿了赋役制度,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明代田赋仍沿袭宋元的两税。税率号称十分之一,然而实际上各地都沿袭旧有税额征收,相差极大,并不以收获量为标准,全国也并无法定的明确税率。如苏州等地,田赋每亩高达七八斗以至一石以上,而浙东青田因是刘基故乡,每亩仅半升。田赋仍分夏秋两季征收实物,一般夏麦、秋米为“本色”。除了米麦正纳之外,还有丝、麻、棉等附纳品目。明太祖即位初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如有五至十亩以上土地而不种桑、麻、棉者,各出绢、麻布、棉布各一匹。除了本色之外,实际征收时又往往折为钞、绢等征收,称折色。
在徭役制度方面,明朝承袭宋元差役制度。凡16—60岁为戍丁,负担差役。16岁以下或60岁以上者免去差役。此外皇室故乡凤阳,官僚、王亲、官办学校学生(生员)都享有免役特权。明朝差役主要种类有:
1.里甲。这是一种职役。明初规定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里中丁、粮最多的十户为里长;每十户立一甲首,十年轮换为官府催征赋税、清查户口、编定户则。在明初,还按纳粮一万石为一区,设立正、副粮长各一人,指派丁粮最多的人户充当,每年押运解送田粮。这也是一种职役。但明中期粮长因赔累而不愿承当(原为世袭职役),改由众小户共同承担,逐渐与里甲混同。
2.均徭。这也是一种职役,项目繁杂,主要是规定百姓为地方官府衙门服役,由于派役时原则上是按丁粮多募、产业厚薄的不同情况分担,所以称之为均徭。主要分为提供驱使奔走服役的“力差”和提供各种办公杂物的“银差”。前者如祗候、禁子、弓兵、巡检、厨役、解户、库子、斗级、仓脚夫、长夫、铺司、铺兵、馆夫等;后者如岁贡、马匹、车船、草料、盘缠、柴薪、厨料、历纸、表笺等。均徭是以人丁为单位的,以后由于力差也往往输银代役,逐渐成为“丁银”,变成了一种人头税。
3.杂泛。它也称夫役,是地方政府征发的种种杂劳役的名称。类似于唐代的杂徭,诸如筑城、治河、修仓、伐薪、运料等。明初规定杂泛以“验田出夫”原则征派,田一顷出丁夫一人,如不及顷,以其他土地拼凑,称之为“均工夫”。沿江地区几府的农民农闲时赴京服役三十天。
明初赋役制度仍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剥削方式。自唐两税法以来,经过宋元明初种种节外生枝,原先户、地税单一,合杂税、杂徭于一的两税早已面目全非。赋役制度又走上了按户、地、丁分别进行剥削的老路。明初对户征发职役,对丁征发杂泛、均徭,对田土征收两税,是这种走老路的赋役制度的典型。明初赋役制度的主要特点在于:土地、人户的清查较为彻底,又使用严酷法律进行威吓,因而能收效于一时。明初明太祖统治时期,出动军队在全国清查户口,编定“赋役黄册”(因上送户部的户籍册用黄纸作封面而得名)。规定政府发给户帖,由人户自行填报本户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田宅、资财、负担的差役等项目,每里订为一册,册首列上本里的户口、税粮总数图表,一里因此又称一图。里中鳏寡孤独免役户、无田户附于册后称畸零户。黄册每十年编查一次,一式四份,中央户部和省布政使司、府、县各存一份。黄册与土地图册“鱼鳞图册”配套,所谓:“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明律在有关赋役钱粮方面违法罪行的处罚都重于唐律。凡人户欺隐田粮,一亩至五亩笞四十,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土地没收入官。缴纳钱粮违限,欠粮人户、里长以上各级官吏,每欠缺十分之一杖六十,罪止杖一百。违限一年仍不能征足,人户及里长各杖一百迁徙,提调主管官吏处绞,以后一般改为人户枷号示众,长官记过降级。逃避差役、投靠官豪之家隐蔽差役,皆杖一百。官府差遣丁夫不平,有一人笞二十,五人加一等,罪止杖六十,等等。比唐律的规定更为详细,刑罚也更重。